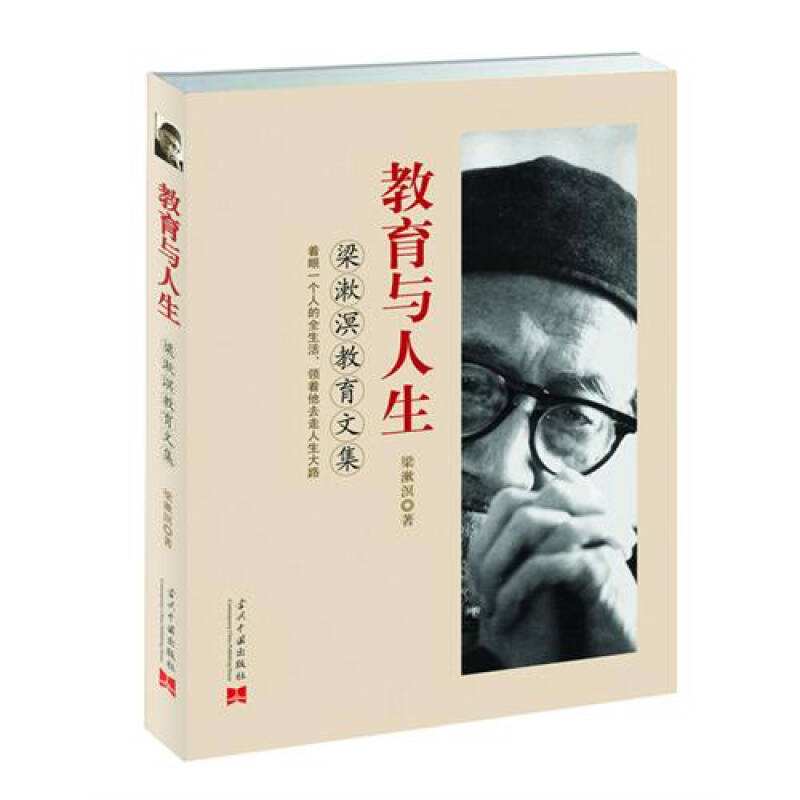109次读书会《略谈人生问题——浅释“践形尽性”》整理稿
主讲:李林溪 督导:李纪川
李林溪:文章不算太长,比起之前《朝话》中的文章长一些。文中所说还是比较平实,不玄乎,不深奥,从字面上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理解。思考题经过师兄润色比之前粗浅添彩不少。开始我没想到能问出什么问题来,但是后来有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中就是:既然我们大家的使命就是“践形尽性”,但完成起来为什么这么难。
冯蕾:文章说得还是挺平白。但这句话我还不是特别理解,就是“形色天性也,唯圣人为能践形”。这其中的“践形”指的是前面说的“形色”吗?
李林溪:不是,我认为的形色就是表象。
冯蕾:形色就是指表象。但是后面说往深言之,后面的“形色”含着无穷的意义,就是指圣人才能达到,才能践形。是指的是这个吗?反正这句话我不是特别理解。
李林溪:当时我看了一下孟子的原文文中所引用的条目是单独的一句话,该条目其没有上下文,没有其他论述来参照。
冯蕾:所以我就觉得整个文章说的是“践形尽性”,所以这句话还是挺关键的。其他的很多都懂,关键这点说老实话我不是太读懂。
梁先生:孔子有一句话叫“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就是说不实践很难登堂入室。孔子大概的意思是:善人质美,但不践迹,也不能优入圣域。纵有好的天赋,不去行动,这还是假的。一个数学有天赋的整体玩游戏,那就玩完了。
我祖父在《人心与人生》里讲得更深,为什么人的婴儿期特别长,需要很多的教育,因为他没有那么多本能。狼不用教都会吃肉,狼妈妈也不用上学习班,因为本能强,学习很弱。很多都是硬件,所谓没有软件安装的空间。正因为人的空间大,装什么内涵进去也不确定,好的坏的都能进入。狼就不会学坏,因为本能就没有这个,学不会。
我祖父在讲儒门孔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我觉得比较得要,就是他尽量用圣人的话去解读圣人。不要自己去讲,不要乱讲。他曾经说过:如孔子者,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不是圣人,我们怎么知道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什么境界。但是我们看他这句话说的,“吾十有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可见孔子在说随着他的生命地演进,他的改变在发生。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至于“立”的内涵,什么叫“耳顺”,容易变成各陈己见地扯皮。无论如何可见孔子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在精进、提高,这一点没有疑义。所以梁老认为解读这些东西,宁肯往粗浅去说,不要往玄妙处讲。往玄妙处说就变成用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圣人,最后孔子的观点被异化,像超市的购物筐,啥都往里装。像从易经里发现量子力学,这就接近于恶搞,最终变成往里加私货。如何避免这样,我祖父的观点要回到最根本的,这一点不会起争议。就像之前提到“吾十有五有志于学”这句体现的是境界随着年龄在提高。如果纠结于“立”的概念、什么是“天命”都成糊涂账,最终成语文课:我觉得是通假,那个说是用典。孔子的真精神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所以《论语》的注释很多,看完之后让人头晕。我祖父讲得我个人觉得让人服气,孔子于此处作何讲,在彼处如何说。比如孔子说 “仁”。我祖父的思路很精到,不诡异,用常识去按照他的思路理解不会与孔子冲突,也不会出偏。例如“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他说你反过来理解就是“惧者不勇,惑者不智,忧者不仁”。忧,就不仁。仁,我祖父说,心安的意思。我祖父阐释的逻辑关系你很容易明白,那就是“仁要不忧”,不是我们理解的人本主义,和孔子的本意又不一样,回不去了。
所以对文中某些概念的阐释要看孔子怎么说,孔子在其他地方说到相同概念时怎么说,要看原著,而非“注”,注解多了就成注水猪肉了。
全贞雪:《孟子》所说:“形色天性也,唯圣人能践行”。我认为“形色”是人本具备的能力,再未实践发开之前只是弱的微薄的接近于本能的能力,但如果不断实践及进步则能发展为突出的超越平凡的能力,而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只有“圣人”能践行得到。
冯蕾:就是说把原来天性中所具有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只有圣人能做到这个。
全贞雪:第一个思考题所问“请分享你曾经对自己的将来所作出的大胆或美好的设想”,文中又说梦想要践行,那我只能说从未对自己的将来作出设想,因为各种各样的梦想都仅停留在脑海当中,没有去付诸实践。小时候想当科学家,但到如今我也未曾为科学做出任何行动,所以很遗憾,对这一题只能回答没有。
李纪川:我说一下“为何在实践终极使命的道路上困难重重”,我的看法是我们选择的道路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这也是我选择拓展阅读的原因。现在这个世界里作为个人来说,能扮演的角色多种多样,如何选择扮演的角色是重要的。做出选择之后,回头路很窄。另外就是在实践道路上能得到的选择很少。
李林溪:我记得先生说过像大禹、孔子这类圣人都是24k纯金的,只是形态有不同罢了。纯度一样,“形”有所不同,“性”是一样的。可能每人在大家心中被铭记的形象有不同。
冯蕾:我刚刚查了一下“不践迹,亦不入于室”。百度上说:孔子说只想当个善良人,而不按照圣贤们已证实可行修养心性的要领和方法下力去学、去修,学问修养就无法达到精深的境界。实际上说就是要去行动,你不按照好的方法去行动就没法活得好的要领。
全贞雪:第二个思考题“曾经的你是否由于某方面的束缚,限制了对自己能力的开发,错过了那个本当?如果有,可愿意分享你的经历或感想”,回顾了一下自己,作为普通人我没有发现过自己身上特殊的能力。我也很想知道奥运冠军们是怎么发现自己特长的?听说有些运动员是从事舞蹈改行打羽毛球,结果还打出了大满贯。朗朗是怎么发现适合弹钢琴的?是他们本人发现的,还是别人发现之后引导的?
冯蕾:我看到文章说奥运会中美运动员的差异:中国举国之力培养,美国很多运动员甚至就是大学生。可能其意在于:美国教育更发挥天性,让孩子在试错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长处,而中国的教育让孩子的天性在整齐划一的教育下变得“泯然于众人”了。
回到第一个问题,如何设想自己的未来,我小时候就喜欢文字,学师范本可以当老师,但因为不想被安排,尤其在看到年级组长家的小平房,感觉不想这样过一辈子。我觉得在自己比较适合的两个方向中选择了从事编辑的工作。从国家单位跳出来,进入一个没有保障的行业,但是对自己内心爱好的坚持,形成了自己职业发展的轨迹。
另一方面,对自己的设想也不是很周到。分享一个故事:当年曾考中央电视台,因为把作文标题搞错了,没有进入到电视台。后来也进入到报社,实习就被分到副刊部,主任比较欣赏我,所以一下就进入到副刊部,没有太多机会进入重要新闻版组。但我自己知道自己是有能力的,但因为畏难而没有跨出自己的舒适区。所以虽然设计的方向是明确的,但也失去了很多成长的机会。
曹凤娇:我觉得发现自己的天赋需要不断尝试、体验,在亲身体验中了解自己适合什么,像在工作中摸索过很多年的人就会很明确的知道自己更适合哪个领域,更想要做什么,我现在正积极的去尝试新的东西,以期发现自己的才能。
子钰:我想说一下“以前对自己大胆或美好的设想”。第一个我跟我爸一说就破灭了。我很想做特工,我爸是搞刑侦的。他说被发现之后会被磨成末儿砌在墙里,我就再也不敢想了。我后来一直想做作家,对文字也很喜欢,一直延续到学中医之后。以后工作也是渐渐往文字方向靠拢,毕业之后做报社编辑,虽然与文字相关,但是我自己却不喜欢。
我对生活挺有畏难情绪,在家里生活出现波折之后,我给自己设置了诸如“身体不好”等限制。我经过调整,也是机缘到来,我给自己重新选择了工作。我觉得大家都是出于在尝试自己合适的工作的阶段。我喜欢写作,有些经历可能在我年龄大之后再以文字呈现出来。现在就是积累,做一些不太牵扯精力的,下班之后就不用老挂记的。我现在做了保险公司内部内勤的核保,这工作需要医学或者刑侦背景来做。和上份编辑工作相比我投入更多,心态也有不同。我的梦想就是业余时间有精力去写点东西。
李林溪:我印象中各种“错过”、“放弃”是有很多故事的。我们都在各种“你不行”的声音包围中成长。我不知天性会被削成什么样子,在历经一代代“修理”之后。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没有被削掉的部分会长出怎样的生命出来,有过此类的设想么?
梁先生:我想起许戈辉采访崔健,崔健说,你看我、王朔、姜文都是部队大院出来的,正好赶上文革爹妈都管不了我们。所以我们就野蛮生长。其后我们的“自我比较大”,被体制磨下去一块之后还剩下不少,所以就还起来了。最近我在做学生心理工作,发现ta有心理障碍的时候,仔细去想,其实就是两个字:恐惧。就是看能不能战胜恐惧,因为所有的恐惧都是主观感受。当你自己觉得“麻烦”、“算了吧”……你自己说不行谁也没法说行。
所以一个人说勇于探索、勇于尝试,你得“勇”。有个经典案例,拿了一个乐器,将其放到低年级学生中,小孩上来立刻就动;高年级一看乖乖的立刻就不动,怕出洋相。探索精神在很小年纪就有,因为ta没有包袱,会不会好听不好听都放在一边,年纪大反而立刻就不尝试了。这就是形成自动化思维,所谓的自动化思维,接近于条件反射,大脑不工作。没经过深入思考就放弃了。“麻烦”、“就这样”……这都是自己的决定。
我想起我祖父在“批林批孔”时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随感而应,行起所当行。他自己的直觉是很纯正的。他不是看某人不高兴,都批判自己,大家都说孔子的坏话,那我为什么还要坚持呢,我也就顺着说吧……并不是,他的直觉,不欺。所以他自己对自己很大的要求就是“不自欺”。不自欺这一点真的很难,开始都觉得不自欺就是对自己而言,但是很多社会的影响加进去,问“怎么办”的关头,你自己能否扛得住。大家觉得很奇怪的时候,你是不是往前走、去探索。
冯蕾:其实小到刚才曹凤娇在群里收到主任短信大家吹捧那事……
梁先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日常生活中一个简单的场景。你想早上几点起床,没有被耽误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起晚了,你就会不爽。谁都不知道有早起这事,你自己还是会不爽。这个感觉非常微妙,但是你自己老是“算了”的状态,你对自己的直觉开始麻木,直觉就开始不工作了。直觉的信号总是接收不到,这个的难度就在这里,就是点点滴滴啊。洒扫应对进退就是修为,也是着力点。这并非唱高调,就看自己能不能做到。非常小的事件,不是说跳槽那种大事件,在点点滴滴中这种事你说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理念越来越强,自动化思维也越来越强。结果就是到那时大脑就不工作了,然后按惯性走,按惯性走就是我祖父说接近于本能的生活了。你把思考的空间就给填满了,灵动和可能也没有了。
说到根本还是勇气的问题。你怕不怕,如果一怕,就退回去了。当然这些很好解释,你也可以给自己找非常好的理由。但自己非常明白,你是在给自己找理由。这种情况下我问过很多人:等到你的弥留之际,回顾你一生的时候你觉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这实际上是很挑战的一个问题。不要说对得起崇高的组织,先说这辈子活得值不值。不要到时候后悔啊,不应该啊,那没用,因为你自己就不断在自欺。自欺的结果就是你把自己的可能性全都毁灭、屏蔽了。最后你自己选择过很low的人生那也是你自己的选择,也不能赖谁。
在自欺的问题上就要问我们的定见和勇气在哪里。没有这两样去谈别的又是一句空话。 有才华、天赋与否可以通过尝试来验证,年轻输得起,老这么混,也把自己给混没了。把自己混得很low你赖谁。
上回说河北井陉两个残疾老人种树,结果河北发大水树全没了。村干部不让人卖树,为了树立形象,为了环保,电视台采访都不许说卖树赚钱。说到这事,有人问为何这两位这么听话。我提出弱势群体,不仅在资源和身体上是弱势,其在心态、思维上都是弱的。如果他思维不弱,他不会成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因为他不甘心。如果他在思维上就是弱的,再有金钱万贯,他也会把自己弄得非常糟糕。自己就决定混吃等死,无论什么条件都能过得一塌糊涂。那些不甘心的就是黑帮小混混,为了当老大也往上冲,是否栽倒另说。但是他不甘心,你可以看得出来。
冯蕾:麻省理工大学有个著名的科学创新实验室,其中一位酷爱攀岩的主任在登山过程中摔断了腿,结果他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给自己安装了带有信息处理功能的假肢,结果登上了原本自己达不到的攀登高度。分享“今日头条”总裁张一鸣发表的《我遇到的优秀年轻人的5个特质》
李林溪:师兄当初给我发的那个延伸阅读,谈到《三体》一书中的射手理论和农场主理论,我读完之后发现我原来对时间和空间的很多认知还是有局限,从思维上就把自己限制了。想问问师兄当时出拓展阅读是怎样的想法?
李纪川:关于拓展阅读:本文节选自《知鱼之乐》,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已经基本浓缩于本段节选,以宇宙发展观的尺度来看,物种的演化过程亦是个体生存能力逐渐弱化的过程,正如分子稳定性弱于原子,多细胞生物对环境的要求高于单细胞,用这个规律放眼人类社会的发展,当代人的个体生存能力没有猿猴,或者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强,一个部落,家族或者村庄或许可以独立生存,但同样规模的团体放在城镇里就需要相互协调以达到资源交换以维持生存;孤岛上的国家或许能够自给自足,但进入寰球经济体内,则有必要进行功能转型,旅游也好,贸易也好,此时的国家作为个体,它的生存能力又变弱了……以上观点来自《物演通论》,作为个体,在这个逐渐复杂的世界里生存能力是减弱了,那么作为当代人,如何在这个趋势下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那一点灵性,是值得探讨的。
个人的观点:未来因为学科越发复杂,所谓“隔行如隔山”,不同领域的技术就像一个个黑箱一般,而学科间的协作越来越频繁,故而需要大量的“中介者”来实现双方的有效交流,我认为知识覆盖多学科,能高效地将行业术语翻译成易于理解的文字的技能是当代首要。
全贞雪:延伸阅读中说:“不光这体质上的残化叫人不得安宁,随后那智质上的分化又将接踵而来。早年的原始人,生活在伊甸乐园,脱胎于动物情怀,逍遥如鸟兽,清明无困惑,此刻人类的精神状态尚属空白而圆满”。如此说,圆满和谐是低等的,未分化未发展的。但东方文化却崇尚圆满和心安,我们赞扬居陋巷不改其志的颜回,那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是低等的还是高等的?他是一直处于黎民百姓普通人的心态,还是从精英分化的人格进一步升华后回到了圆满状态?
梁先生:对于颜回这事,大家都感觉安贫乐道、不思进取。这容易产生歧义,我倒想起对于我祖父当年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在文革当中,1966年8月24日就被抄家了,但他在9月6日写完《儒佛异同论》的“论一”。他心安,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心安,他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看到颜回就在陋巷里忍着了,看不到他积极的行为。“一箪食,一瓢饮,回不改其乐”,饿着就饿着。
冯蕾:他可能没有写颜回的背景。
全贞雪:距离颜回的时代太远,我们不知道。
梁先生:我觉得我祖父在文革中这段经历说得就比较清晰。在如此大的冲击之下写完“论一”,可以想见他在几号动笔。看他的日记早上要被勒令扫厕所,白天要开他的批斗会,他仍然还要写《儒佛异同论》,这就看出他的定力。艾恺有本书说我祖父是“The Last Confucius”,有人说我们还有很多儒者,艾恺说你们是儒学工作者,他是儒者。你们是靠儒学吃饭,他是靠儒学生活。艾恺问为何我说他是“The Last Confucius”,就问你能否找到像他那样生活的人,不管是专家还是高手,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北大的王宗昱教授说我们为何钦佩梁老,因为我们做不到。不是说出书、上电视等,就是你有没有经历他那种生活。
冯蕾:如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特别明白的知晓自己要什么是挺幸福的。这时候你才知道怎么去坚持。
全贞雪:是否因为某方面的束缚限制了自己能力的开发,如果这个束缚是看得见的还好办,有些束缚是无形的,自己完全发觉不了就如父母给的影响。有篇文章就说,我们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像自己的父母,这种影响完全融入进思维、习惯、生活中,不让人所知觉。比如我自己在大学填报志愿时就选了医学和农业,因为我父母从事这两个职业,虽然我对这两个职业的了解与其他人无两样,但在填志愿时莫名其妙的倾向于这两种。不止我如此,很多运动员也是因为父辈从事运动,后来自己也走向了运动生涯。感觉这样的影响与束缚是如轮回般是很难超越的。
冯蕾:我丈夫是在福建上的大学,他的同学全是自己做老板,家里就有这个做生意的环境。人是环境的动物,上一代可能由于环境的封闭,基本上没有更多的选择,有时一家人都在一个单位,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但下一代孩子会有更多的可以试错的选择。
美国教育教会孩子的是“不惧怕”,不惧怕失去,创新的最大障碍是“求稳”心态(见分享的微信文章《留美15年,遇到一群奇葩,他终于参悟了美国教育的精髓》)。
问题是我们可否一辈子安全?现在那种封闭的环境已经不存在了,只能选择自我奋斗。
梁先生:原来讲课时我说过,个体放在中间,一边是发展,一边是安全。太安全了发展就成问题,和骑自行车一样,下了车肯定摔不着,只能走了。我祖父说你把可能性全部干没了,一切都安排好了。最经典就是采访陕北放羊娃:放羊为啥?娶媳妇。娶媳妇为啥?生孩子。生孩子为啥?放羊……你不能说他不安全,但是可能性没有了。其实你可以发觉大部分人到了一定程度会受不了。反而言之,这样弄,自己会被吓着的。
我曾经去上海讲课,我们同班同学是党委书记兼校长,安排学校司机送我。有另外一个校友就说不让学校送,要就自己送。我知道他有事想找我,这校友在学校就已经是教授了,手上可能有两、三个公司,都挺挣钱,搞工科出身。他说女儿上初二,各方面都很棒,家里也有条件提供各种可能性。有一天他问她就有一种要哭了的感觉。他的问题是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女儿说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当爹的自然要听真话,我又没让你写作文,就说你的真实想法和愿望。女儿说想成为一只生活在两大堆大米中的米虫。就是那种混吃等死的节奏,这一定有她的问题了。我做咨询之后感受特别直接,很多初二的女生开始厌学,她们的成绩并不差。一般说都是乖乖的,成绩一般不错,理论上跟着走就行。可是就是走不动了,她对人生的意义绝望,自己无法向自己交代。压抑和欺骗自己已经干不动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女孩老说我总得学习啊,其实已经学不进去了。她也不办理休学和退学,但是学校不能让你这样啊。她自己老说那不行啊,不学习怎么办啊,我说那你现在也没学习啊,你怎么办了……
这东西看着就非常冲突,标语在那,自己在这,她没办法,站在中间两头都不撒手。她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就在那混。后来我理解为何男生出现得就少。男生这种情况就是去你的我不去了,我去闯社会。女孩是又怕,又不愿意,成了一种纠结,不像男生那样豪言;我靠着打游戏也能挣钱。男生敢说,女孩不会想这个。自己会想不念书我没辙,但是念书,我又念不动,就自己和自己斗争,成了问题。男生管他网瘾不网瘾,打就完了。女生就比较拧巴了。
子钰: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梁先生:一定要让她回到自己。问她“你不上学,你说的学习是什么意思?”“有意义为何不学,要学习为什么不去教室?”还有听课和作业的问题,不能一边喊着上学,一边却什么都不做。行为和主张是冲突的,要解决就得让她直面。就是要退学,包括问家长你敢不敢让学校开除。不去上课又没有病假条,那就是旷课,休学都不办,这是绝对的自欺。哪个学校都不能忍受挂着学籍不去上课?这就是典型的自欺。
所以这个意义上我对tg的主张,对人心灵的戕害太严重,二十四字真言啥的最后都没法弄。包括徐不薄、方便面都是模特队的人了,其中有个去看老领导,老领导退下来了。这人就说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敢说真话。老领导说你当我敢说真话,我也不敢说。不说别的,这心理上就不健康,他自己就是冲突的。几十年不说真话,所以徐不薄最后癌症挂了。我看专业美国期刊的观点就是:癌症是大脑对身体的暴虐。身心不统一,老打架,比如恩夹,恩夹不得癌就怪了,自己对自己攻击会出问题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任强调对人性的最大呵护,害怕资本对人性进行迫害。不管着眼点的问题,他的关注的心态是对的。但我们TG好像就不对了。又有一个战士胃出血倒在工作岗位上。那是不是比资本更变态,自己把自己干掉了。我这个主义特别好,根本的内容就是拿人不当人。
马克思特别担忧就是资本对人性的异化和戕害,我们现在不是用资本去践踏和戕害人性了,你就有道理了么?其实没道理,不用吸毒来戕害健康了,酗酒一样也是戕害。说酗酒好,不抽白面该酗酒了,也不能这样。这就背离对人性基本的尊重,和主张没关系。里面可能有谋私利,但这是愚弄了大家。光说那些抛头颅洒热血、讲献身,如果他能看到徐不薄和康师傅没得哭。本质还是要对人性有尊重。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单位为了搞“两弹”,组成敢死队。明明知道有污染,就是不戴防护,为了表决心。有人金属铍中毒,我因为科研成绩被提升为研究室工会副主席,到医院去慰问病退的员工。阜外医院有职业病治疗专科,全国9个铍肺,7个在我们研究所,
冯蕾:他们后悔吗?
梁先生:他们悔死了。他们的肺几乎不工作了,氧流量开到18升还觉得憋闷。有个女同志叫郑秀芳,因为肺积水,跪在那呼吸。有一天早上接到电话说她自杀未遂,她自己感觉活不下去了,太难受。她这个属于特例,就是西洋参都报销,但这管用么?阜外医院因此写了很多论文。
特别触目惊心,我离开那之后又发现两个。他开始胡整,没有防毒面具带一个猪拱嘴也行。结果为了TG就直接上,或者多戴口罩,或者勤着换人,但都没有。
子钰:之前他们知道没有防护会有问题么?
梁先生:会有问题,但没预计到那么严重,戴防护也不影响工作啊。既不多戴口罩,也不勤换人,就因为是敢死队就胡整。这真的符合TG宣扬的精神吗,我觉得就不对了。我印象深的是开始得一个月送两瓶纯氧,后来不行就一周送一瓶,再后来就送阜外医院了。后来说为了方便把女儿也招到我们单位,我注意到,特别还问过,牙都是紫的。
冯蕾:牙是紫的?就是她妈妈怀着她的时候就中毒了?
全贞雪:体内有一段时间的蓄积,后来生小孩就有表现。
梁先生:这东西接近于胡闹了。
全贞雪:矿上工作过的尘肺职业病患者是职业病医保范围,在用药上比别的病人宽松很多,甚至有些药物超指南超常规超长时间用药,监管也很松。这个乱象好像历史悠久,只是让当前临床医生堵抢眼纠正乱象是完全不合理的,病人的嚣张气焰很盛,出于医闹的畏惧,目前医生只能从其要求,但求了事。乱象就说明有一定的模糊地带,不是单一方面造成的。
梁先生:很多东西一算细账其实不值。最后我们这个老郑故去之后就开始PK,非得进八宝山,我说那我也管不了。到后来就越发荒诞了。
冯蕾:回到刚才说到的初二女生,很多孩子有厌学,怎么能避免这个。
梁先生:家长首先得明白。学校在“格式化”学生的时候,家里有表达通道,孩子是可以表达自己的。
冯蕾:如果孩子不喜欢学,他会因为有表达通道而改变吗?
梁先生:最起码我们可以看到他性格不舒展。这种扭曲一定是跟家庭环境有关系的。因为家庭是既能让他扭曲也能让他发展的。如果始终强调不论如何都得高考,那他就被格式化了。
冯蕾:孩子没有渠道去宣泄自己的想法。
梁先生:所以我觉得那孩子身心分离那么严重,当妈的还在吓唬他呢。我就说学习成了他的一种恐惧。他母亲还说,你还不跟上这个班,到了另外的班,那个老师比这个还恐怖,这还是恐惧。这个恐惧就是“先把初中读完”,目光集中在初中毕业证上了。她闺女也就被这样陷入其中了。如果当妈的心疼孩子,去他的,爱怎么着,孩子舒服了在说,咱不能扭曲。在这个时候因为孩子弱,家长自己做主了,孩子自然也好,而不是嗷嗷这么整。所以这一定是家长的问题。看一个最简单的农民工,说不念书干活去,他不会扭曲啊。
冯蕾:我觉得我们家孩子中考完了那个问题解决了,我们也是释放他。他姐姐是念外语的,今年开学去英国读奢侈品管理了。他自己喜欢画画,又觉得设计之类挺好。他在回答学校的一系列问题之后,他写我希望将来从事与时尚有关的工作。他自身的表现就是对头发、发型感兴趣,剪头必须去找指定总监。比如今天回来我为何跟他嚷嚷,他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头发,洗完头发那一堆的内裤袜子扔在那里,自己就回到房间里去打游戏去了。我能理解他打游戏去释放自己,但是从事时尚,去国外是一个分分钟被饿死的职业。我是应该顺着他让他自己去试错,还是我应该一定程度上给他指引。
梁先生:还是得让他自己去成长,但是这个过程中你用信息去引领他,让他去了解。他可能看到一个表面,对内里不了解,你可能提供更多让他看到内部的东西。让他自己去看,自己判断。我们要明白我们对他的影响一定是越来越小,不会越来越大。随着孩子成长,你的影响在减少才对,他对你越来越依赖就不对了。对你而言还是要回到原则上,要相信他自己,你要做的就是解决最基本的条件:他能不能去探索,能否有勇气。有没有勇气和能力把这个问题看清楚。你只是焦虑于此,而非他具体做什么。
冯蕾:我焦虑的就是我没法给他恰如其分的指引。
梁先生:不是,这还是你的恐惧,还是你的信任。你不相信他有独立判断,而且有“我不帮他,他掉沟里咋办”这是最后的潜台词。
曹凤娇:我现在特别讨厌我妈不信任我,感觉特别不舒服。
梁先生:这个感觉,包括践形尽性,肯定包括对自己全然的信任。孔子没自信他成不了孔子。问题是怎么能培养他的自信,而光是我来给你下这盘棋,这是不可以的。
冯蕾:我觉得他能进到北大附这个学校,我心就放下一半了。这些同龄伙伴都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的,不是那种两极分化很大动不动就被坏孩子带沟里的。
梁先生: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你要解决就是不断去培养他的勇气。有勇气死磕也能磕出来,无非就是磕一百下还是八十下他磕明白了。我们老觉得是分数,那很直接,但仔细一想,没有勇气什么都是白给。到最后很快就不行了。回到本质上就是,他得去实践,去体验才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