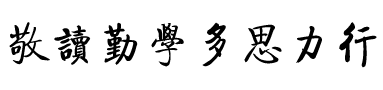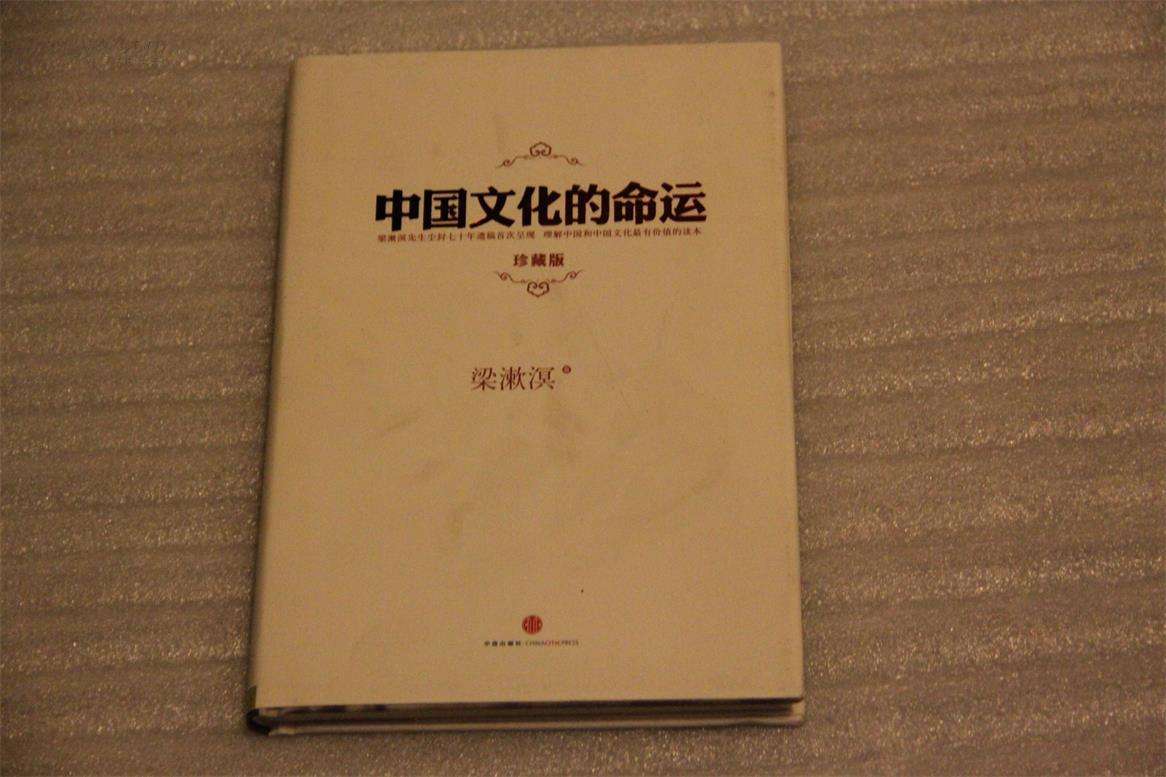第110次读书会《中国文化的命运·西人所长吾人所短》整理稿
主讲:李纪川 督导:全贞雪
题目1,:在讨论公德的法治精神方面,梁老引西人之执法同国人之徇情做对比,似乎中国人从来在处理大团体内矛盾的时候是参照家族宗亲间处理矛盾的方式,故尔“法外开恩”成为中国式法治的常态,“法”本身的权威性亦被扮演“家长”角色的官员兼并了。思考:在法治社会的今天,这种中国风格的法治仍客观存在于我们身边,你认为它是社会向前发展的桎梏,或是其中隐藏有某种中国式的智慧从而延续着它的生命力?
全:若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这种状况恐怕会一直行得通。比如我们在医院给患者抄外院处方,本身违反医院管理制度,大家都不乐意干,一来要担责任,二来没有技术含量,这类活使医生对自己劳动的尊重感下降了,医院也是明文规定不能抄方。但这种规定的对象是大部分患者,若单位里穿着白大衣的同事过来要求抄方的话,总难以驳人面子,拒绝行这个方便。然而这种事若是放在社会的大环境中的话,亦没有规矩可言,全乱套了。在中国生活,完全不顾情理,很难相处,容易被群体孤立。如北京的公交卡有学生卡和社会卡之分,一般学校里会有借用学生卡出行的情况,我大学时有个同学遇到如此情况,曾说:这个卡是规定给本人使用的,我若借给了你就是违法,所以不能借。身边的人马上会认为他很“膈”(ge三声葛)不好交往,故而多选择敬而远之。我觉得在中国的环境下如此特立独行严守公德有些得不偿失。
冯:我在想这种中西差别是否和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的形成发展有关,欧洲的海洋文化在形成过程中造就敢于冒险的风格,且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比较明确;而大陆文化安全感优于海洋文化,靠天吃饭,因为不一定年年丰收,也没太多地方探索掠夺,故而储存粮食和资源尤为重要,容易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模式,类似封建制度,故尔这种家族式的经营管理模式容易发展,但不知西方或者其他大陆文化的国家是否也有中国“徇情”的现象?或这种缺少公德的现象是怎么回事?我曾经在加拿大经历大雪,当地很早会有人把社区行人的道路清理出来,一直通到当地社区的车站,而早上上班的人们都很自觉地排在这条路上,每次公交车到站,能上去的人很有限,前面的人鱼贯而入,等司机说满了,剩下的人也绝不会往上挤,都跟着排队,这种现象在当地随处可见,而在中国绝对是另一番景象。又如我有一个南方同事,说话习惯声音很吵,时常造成我们同行者的尴尬。
川:刚才您谈到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我想到一点,即海洋文化主要是探索未知,但大陆文化,或者农耕文化的规律性更强,我认为从逻辑上讲,大陆文化更容易形成因认识天地的规律性为主产生的法则,我有些想不懂为什么存在于这种更容易孕育“法”的环境下,中国人反而不遵法。我后来思考,可能是家族式的经营方式使得族长或家长逐渐变成了法的解释者,或法的代言人,在这里有人等同了法,故而有了感情的漏洞,这种情况逐渐变成如今的现状;海洋文化中,如若远洋探索,一艘船的船员搭配很重要,除了船长,得有瞭望,有厨师,修补匠,大家各司其职,每一次出航就是一次团队的协作,本身不存在一个人全能,这种团体协作可能慢慢就变成这种文化的烙印。
全:大陆文化因为尊天地,可能更容易形成“顺”的文明性格,天高不可攀,故而……
梁:这个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除了社会,人的相互关系以外,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把我们都带沟里去了,有很多基本概念上的错误,是严重的偏差,可能编书者有自己的企图,故而把书编成如今这番模样,也把我们整个误导了。比如所谓封建社会的定义,其实严格按封建制度去考察,其实基本上秦始皇之后就没有封建制了,西周,还算是封建制。我叔父讲过一个趣事,在民国初年,可能对老百姓是非常苦的日子,但是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因为军阀割据后,思想多样化,因为无从统一,比如蒋介石想整你,那么我跑阎锡山那边去,或者冯玉祥,李宗仁那去,这样就有战国的味道,虽然上面盖了块名为“中华民国”的布,其实底下是一簇一簇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思想是活跃的,也就是说蒋介石他当时并没有办法一竿子插到底,后来抗战以后,通过抗战这一事件,形成一个领袖,一个国家,一个主义,才把军阀给铲平了,否则底下是割裂的,割裂的结果就是上面的专制非常困难,但是秦始皇他真是一竿子插到底,皇上要抓谁那立刻就得抓,但你看战国春秋时期那是做不到的,合纵连横这些事大家都听过,他可以来回跳,所以思想是活跃的,或者说多元化是有保证的。我认为秦始皇后应该叫皇权专制时代,皇上一个人一瞪眼,就全完事儿,任谁都没节目了。
大家可以想明朝是怎么垮的,明太祖朱元璋对皇族的那个态度,皇室生孩子生到朝廷都负担不起了,皇室子孙朝廷供养,他生一个就给钱,然后又怕重蹈朱棣燕王篡位的覆辙,比如你们俩皇室兄弟,但是不允许串门,不能见面,只能自己呆着,那只好生孩子了,余了啥事儿也干不了,所以就使劲生,反正朝廷给钱,所以后来有的亲王上百个孩子,这样的结果,或者说政治架构造成整个社会被扭曲了,那所谓“朕即国家”,其结果就是你一人敌天下,你拿一根草都是拿我们家的,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皇帝)得把所有人都当做贼来防,那么他的那种深深的焦虑是永远无法释放的,他要和大家为敌,所以大家也就不得不抱起团来跟他作斗争,所以大臣们糊弄他也好,给他做局也好,那就只能一直玩这种掰手腕的政治游戏。包括朱元璋不允许设首相这职位,那后来的大学士还是出现了,因为这事儿得有人来干,除非你想把自己给累死,所以还得有这个职位,但是又会分权,分权又和他高度专制的期望矛盾,他自己给自己玩了一个好像猫捉自己尾巴一样的死局。这种情况也造成了社会的散状,比如清末时期国库紧张,有大臣建议开矿,那肯定是一个致富的办法,但马上有人上书反对:您忘了太平天国了么,那就是因为开矿,这些无业游民一聚集,就要出事儿,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百姓原子化,即最好没有团体,一有团体统治者就害怕,所以当时有“君子朋而不党”的说法,结党是会被灭九族的重罪,所以就是这个局面。
再说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我觉得可以再往深处讲一步,就是工商文明和农耕文明,你不论是否沿海,只要推行工商,就得有契约,再一个是双方自愿交易,这样的结果就是行会的出现,比如铁匠协会,鞋匠协会等这种横向的组织团体就崛起了,尽管最开始可能只是经济利益,但发展之后就逐渐有政治诉求了。另外一点,工商文明的根本,大家为了获取生活资源一定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一定得有交往,故而一定得有公德,没有公德,则交易无法实现,不是觉悟高,而是只要要做交易,那称就都得准,你给我使假称,我也用假称,那最后大家等于白玩,后来就明白了,所以这些过程里不是因为觉悟高,而是这个生活的过程带来的东西使得你意识到这种玩法“没劲”,或者都被淘汰了,那么优秀的商家一定符合商道,符合业内的规律才能崛起,否则就会被淘汰掉。他们是在一个非常严酷的日常生活当中被锻炼得有公德,不讲公德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农耕文明不然,比如我们一个族里的一条心,到外面坑他们村的,这个好办,一下就能抱起团蒙人,争地,争水源,照死了打都行。换做工商文明,我的水要从你那里买,你的粮食要从我这里买,大家马上就明白这种东西是没法玩的,所以你可以清晰的看到什么咱们应该抵制日货的说法都是很蠢的农耕文明的思路,工商文明他一定明白这是脑残才想得出这主意。但是因为深深的农耕文明的色彩,而且你若替皇帝来想,皇帝也会喜欢,因为可以有效的把大家都原子化,另外皇帝的脑子也不够用,他想的逻辑是你种地,你就有饭吃,;你有饭吃,你就不造反;你不造反,我就没事。如此的一套把戏,所以他特别反对工商,一工商他就有交流,一交流就难免会有各种各样我想不到的事发生,所以你最好给我拿着锄头,他也拿着锄头,大家都在地里别出来,种,种,种。年底我一收租子拿走,然后你们接着种。故而皇帝始终不肯把工商的创造摆到主流位置,哪怕是作秀,他也要去神农坛,他也要摆一个在耕地的pose,鼓励大家好好种地。即便扬州的盐商后来富裕起来,但是其社会地位仍然不行,皇上不给社会地位,因为他会担忧其中深层次的问题,因此没有保护工商贸易的法制,结果就是工商贸易在中国没法玩,因为每个行业需要有行规,就如长白山的挖参人就有约定,谁发现了参,在上面栓个红绳,其他人就不会动它了,这中间没有法律,但是有俗成的约定,大家都会遵守,否则没法玩。打猎也是,只要打死了,就不要动,那是人家的,这些都是自律的,没有强制,因为如果乱着来,最后大家所有人的打猎效率都会很低下,谁都都活不成,他不是人的道德水平突然上升了,而是在这个行业里如果你不按着约定玩,你最后就把自己玩死了。慢慢的,从遵守规定开始,信任也逐渐建立起来了,从这里我想起祖父所说的:讲孔子,不要从高深处讲,不要往玄妙处讲,最好往粗浅处讲,就是他的生活,孔子的话要回到他的生活去验证。因为孔子那时候没有琢磨那么多形而上的东西。放到公德这里你也无从讲出多么高尚,因为他的文明的发展必然要走这条路,所有工商文明只要有双方面交易,造假肯定行不通,弄个假称糊弄人都是单方面交易的玩法,那么中国的皇朝正是严格限制了工商的发展,造成了皇家单方面交易独断,他可以利用皇权来玩不平等交易,那么底下的人也互相耍鸡贼,结果就是正当的平等交往是不存在的,那怎么办?他就要变的畸形,我记的几个历史场景很有意思,姑妄认为他是真实的,也许有出入,但我考虑大致应该不差。宋太祖赵匡胤和大臣对话,那个大臣站起来讲,上前一步启奏,等讲完该做回原位时,发现椅子没了,赵匡胤让人把椅子撤了,所以从此以后,大臣都得站着上班了,到清朝就得跪着上班了,所以你可以看出,君臣的关系已经不行了,又比如朱元璋,他恨孟子恨得牙根痒痒,孟子他讲社稷,谁重,君,谁重,老百姓,谁重,朱一看,这不是造反的节奏么?而且孔子也将得清楚:君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人家不玩了。那在皇上看来,你们都读了孔子书,都这么弄,那我怎么办?这不是耍我么?所以这个时候所谓三纲五常,乱七八糟的东西才出来的,那些个和孔子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孔子是真正的封建时代,他不是皇权专制时代。所以我们(历史书)就是一锅浆糊,这锅浆糊给你弄出来了,你就喝吧,喝完还觉得挺好,好消化,但是你仔细一想,他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正是战乱的割据使得思想多元化,而不是大一统,高度大一统的结果虽然是车同轨,书同文,实际上最后思想也要被钳制,不钳制他就不安全。所以你也别给皇帝抹黑或者镀金,仔细一想就知道他得生活,人家也得生活,所以还得回到生活层面上来。
再说到明朝倭寇,他海盗为什么要去攻城,那说明他们不是盗,他要么就是造反,要么就是报仇,而且是血海深仇,跟你死磕,那如果说仇的话,他说得通,但是日本倭寇,和明朝官府能有多大仇恨,这你怎么也解释不出,他一定是跟他近的人才有仇,对不?我跟你不认识,咱们一辈子没见过面,互相有仇这事说不通,他一定有前因后果的,所以咱们学的历史,尤其中学历史完全是乱七八糟,把大家都带沟里去了,使得我们对社会,对人之间的信任和认知都搞混了,所以后面他再忽悠你才方便,不然他不好忽悠,否则他没法解释。所有专权时代一定有海禁,靠海的老百姓因为活不下去了,那就造反,就这么简单,你包括太平天国,你这么弄,弄到最后,其实和DANG是一样的,一开始你可以用一个信仰,一个空泛的信念带着大家跑,但是跑两步以后就麻烦了,柴米油盐酱醋茶,饮食男女就得浮现,你不能老忽悠啊,你得兑现啊,所以他最后就弄不动了,他的男营女营就分不动了,大家都跑路了。不论你这个主义多高尚,都得回到人上来谈,中西人的不同,是源于社会发展的路径,和社会运行的形态不同,带给我们这些差别,根本不是觉悟高低,西方的工商文明已经玩了几百年了,我们没玩,还弄了个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很美好,看上去很好,也给我们舒适感,有DANG和国家做底气,但带来的问题就是大家对自己的责任担当的意识变弱了。
大家可以看,德国最大的产业是什么,德国为什么欢迎难民,因为德国最大的产业是社会救济,德国那些被救济的穷人的住房面积优于中产阶级,德国法律规定底层经济实力居民的居住面积为人均45平米,而很多中产阶级都是做不到的,结果就是它这个形成一个行业,这些人为了不失业,我们需要有新的救助对象,难民来了,就是我们的新客户。像这样玩着玩着就把自己给玩死了。你不要想什么觉悟高低的问题,这一大群(救济行业)人他们都投票,有选举权的。我们大多数人被训练的都是直线型思维,即因为……所以……,只要……就……,滑稽得很,那结果就是大家一起不工作,混吃等死,因为中产阶级可能工作半天过得不如被救济的人。所以(看发展水平)最简单的方法是看社区的环境怎么样,当大家都是混吃等死的时候他对环境是不会在意的,和他生活水平是无关的,他精神上是萎靡的,所以他要不是养宠物多,要不是满街的脏乱差。另外德国的这些低保人,往往是最新潮电子产品的消费者,因为中产阶级忙生活,没工夫去琢磨这些,所以德国超市里贴的标签都很有意思:“你知道我并不傻”,这事很颠覆,就像社会主义,你走着走着他想不到的事就出来了,当大家一起混吃等死,那这个社会会成什么样子,曾有调查,中产阶级家庭和社会底层家庭的儿童,同样年龄段,比如6岁之前,前者的孩子接触的单词词汇量比后者多大概三十万字,因为你生活是多彩的,要是家里竟讨论又该领低保了,谁家又领的多点儿,晚饭弄个什么香肠之类的,因为他就这么些词汇,就是混嘛,你也听不着新鲜的,那结果你长起来以后你学到的也就是混,他没办法,他突破不了。所以这些现象要接地气,要从生活考虑,因为不管阳光面还是阴暗面,他先是人,这是人类社会,不是驾着五彩祥云的社会。
曾经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平等,当现代互联网来了以后,商业社会以后,大家是信息平等的,你不能忽悠我别看什么书,办不到,特别是广泛交易过程中,以独立家庭作为核算单位进行经营的时候,他必须得对自己负责任,他糊弄就分分钟完蛋,包括手艺的传承,比如做小提琴的,你糊弄,糊弄完就死了,你做一把坏琴,招牌给砸了,这一个家族就没饭吃了,所以你必须全力以赴,他可能是自私狭隘的,但是他是认真的,是不敢糊弄的。但是一旦变社会主义了这事就麻烦了,这反正不是我的,社会主义造成最大一个问题就是零成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但最后还得有人买单,你一定是占便宜了,他不见得通过剩余价值来解决,马克思在狭隘层面解释了剥削,但其实不是,比如啃老也是剥削啊,它不存在剩余价值,一个概念如果太狭隘了就变得诡异,而且无法自圆其说了,自己就破产,你回去啃老也不存在雇佣关系,但这难道不是剥削吗?他仍然是剥削,他也不是阶级,不是说必须有阶级才有剥削,穷人也可以剥削富人啊。
生活就是这样,可能很残酷,但是如果不能看清楚,被误导,就会很糊涂,但是这些东西绕不过去,你想在思想上不犯错误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思想,所谓我们要给正确的言论以自由,结果就是没法说话,最后这个民族就会变得非常委顿,就站不起来,北朝鲜就是极致化的路子,他所谓的人为主体,这种思想就是和自己打架,没法自洽,不得已搞出来个白头山血统云云。
全:在中国社会不讲人情很难,因为就如文中所说我们自古就习惯论情。人情社会中“你与我方便,我与你方便”,成了礼上往来。在小环境里,在小事情上,论情似乎没有什么后果,但在大环境里,还是没有秩序充斥着人情交易,肯定会妨碍社会发展。在中国社会要坚决遵守公德,拒绝人情交易,也是十分难做到的一件事。
有时候患者拿着别人开的中药方找我们腾方子,腾方子是一件很伤医生自尊的一件事。估计国外的医生是坚决不做的,听说外国医生最痛恨的事是外力操纵自己的治疗方案。作为中国医生也从心底里不愿意抄别人的方子,因为抄方子不能免除自己的责任,只要患者服药后出问题,方子是不是抄的都免不了责任,因为处方上签的是自己的名字。更深层的心里层面的问题,抄方子是被动行为,感觉被人指使,自我受到了伤害,从心底里不愿意做。如果来抄方子的是患者我们会坚决的决绝,说有规章制度,但是来的是同事,就很难拒绝,如果驳面子以后的同事关系不太好相处,所以不得已放下身段屈服于人情关系。但大环境下全是人情关系那社会秩序将严重被扰乱。
梁:这是全民的基本无意识,而这种无意识的背后就是恐惧,怕出错,出错自己就完了,这样的结果,就如我所说,好使,行动力最强,一吓唬就得了,这种方法持续下去,一直这么弄,其结果就是我们对这种恐惧深深的控制了,人们一旦被恐惧了,智商立刻就变零,所以创新就变得格外的艰难,因为创新就一定要犯错误,一弄就成一碗那不叫创新,那是捡漏,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GDP搞上去了,但是国民自主的意识是否起来了,从朝鲜半岛的南部看最明显,一开始还有光州事件,但他现在再也不敢动武了,他也意识到了,现在反对萨德也敢上街游行,但是DANG哪忍得了这个。
全:中国人自古以农耕为主,靠天吃饭,所以对天的敬畏更甚于其他民族。农耕的经济形势,使人更深刻的感受到顺应天时顺应自然的好处,因而我们容易成为顺民,当有人以天的名义(天子)发号施令我们更容易臣服。
梁:包括电信诈骗,我在想,这些(搞诈骗)人到美国去得饿死,因为美国人对国家机关这些权利机构没有那么强烈的崇拜,不会说一个电话让我交钱就交钱,打来先找我的律师再说,不会对权威有绝对的迷信,现在(诈骗)都是打电话说我是公安局,我是检查院等,都直接是权力机构,利用这些机构的余威来作案的,所以也就骗大陆人,你拿这一套骗香港人,美国人都没用。我祖父分析这个,有族民无市民,是在生活当中,你就得这么做,不然你过不下去,这一点就讲的非常清楚,(古希腊)城邦国家市民就是公民,那个时候的国王很可怕的,希腊的城邦以前还有民调,一旦你的军事将领的民调过高,马上就把你抓起来流放,防止你专权,他的政治制度设计的就是要消灭英雄,他们在文明的价值取向上就把它(英雄主义)给PASS了,他的制度不允许,他意识到在那样的国家里不能这样玩,一旦你弄(专权),马上把你关起来圈5年,跟外界隔绝,基本你的威望归零了,再放出来,包括拿破仑也是,他是(关的)年头太短了,一出来又东山再起了。相反你看起来这好像有些冷酷,但是他并不是在肉体上消灭你,他只是流放,或把你关起来,包括列宁都是,他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都有图书馆,那是沙皇对付他的死敌的办法。滑稽的是,那些皇帝也没有学过仁义道德,反而还有点人情味,(反观中国)动不动就灭族,这种反差太大了,我认为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族民还是市民,也就是工商文明和农耕文明的问题。雍正给自己画像都画过自己是老农,他从没把自己画成商人,中国极度轻商的结果,一个是中国整个发展不起来,因为没法交流,思想,文明都是需要交流的,汉唐时代极度开放,文化多元,交互刺激和流动,而越封闭就越完蛋,包括生态系统也是,一旦(和自然)隔绝了,被卡死了,那个系统也就死了。我们自己要明白,知道怎么躲开伤害,别被忽悠了。
2. 在谈到组织能力时,梁老特别指出中国人或为顺民,或为皇帝的两种极端行为现象,甚者赌气掀桌,即缺少团体向心力和耐烦妥协精神,你在日常生活中经历过这种一山不容二虎的情况么?你认为作为团队的领导者或团队内的矛盾当事人遇到该类情况最合适的处理方法是怎样的?
梁:可以从广义来解释,(以前)除了皇帝组织的其他都是非法,他唯一能组织的就是军队,这事对皇帝也很挑战,说(战士)打仗是为了皇帝,这事也说不太通,农民是因为我惹不起你,所以你让我干啥就干啥,军队里没有什么凝聚力,都是一个路子,(士兵)本心上没人想去(服兵役),特别是这种大一统的国家幅员大了以后,情况就变化了,比如北方的匈奴攻进来了,我在江南种地呢,(入侵)这事跟我有一毛钱关系么?他所谓保卫国家的感觉就更弱了,因为大家都是原子人,鸡犬相闻,风马牛不相及,他和什么燕云十六州的人更没啥关系,所以打起仗来就更没劲。除非你的军饷给到足够,他愿意去拼命,那是另一档事,但是即使是为挣钱,那他凝聚力还是差,毕竟要留着命花钱,所以中国古代的战争很有趣,他一般只有围城战和击溃战这两种,比如赤壁,很少有西方那种照着死了砍,直到一个人都没有了,这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西方的战争伤亡比较好统计,因为算尸首就成,比如这波人上去然后全死了;而中国的战争一打起来,人就没了,可能投敌了,可能跑路了,不一定死了。
这需要从具体战役看,中国中学历史最大的弊端就是全是宏大的政治叙事,没有细节,结果就是你很难辨别他的真假。西方的经典战役,比如希波战争,斯巴达300勇士死守温泉关,这300人,干掉2万多的波斯人,就是死磕,最后被灭是因为波斯领袖薛西斯收买了一个希腊政客,抄了近道,把这300人包了饺子,才灭掉。他们把住隘口,生生堵住了号称10万大军的脚步,而且300人杀2万,光砍也很辛苦的,但是砍完了。再一个马拉松战役也是以少胜多,那么之所以希腊人能这么打,就是因为军队没散,而(中国)这些一触即溃是因为军队的组织架构被破坏了,彼此没有信任和相互保证,大家都跑路了,正如我祖父所讲,他缺少组织,都只不过是为了那二两银子的军饷,没必要拼命,跑了得了。那波斯人打进来以后,破坏了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要捍卫自己的主张,可能我们被占领后就从自由民变成奴隶了,所以不能让他们得逞,必须死磕,这时大家有共同的信念。当时的希腊国王也很痛苦,斯巴达国王尼奥尼达斯,他就干了两年,都轮流执政,而且有俩国王,一个管内政,一个打仗,换的时候俩人一起下,所以说希腊的政治制度很奇葩,如黑格尔的评论:希腊的政治是一件艺术品。但是西方文明的缘起离不开希腊文明,但他之所以生成,还是工商文明,他一定不是封闭的,特别像威尼斯这样的地方,封闭了就死路一条,弄海禁就等于自己勒死自己。
但是中国能够自给自足,“我天朝上国啥没有啊。”确实是,这样的形式构成(皇帝)容易有闭关锁国的冲动,他没有诉求,他就封。但威尼斯没法这样弄,正如所谓上帝的诅咒,所有资源型国家都发展不起来,包括俄罗斯,他自己也转不了型。可是像德国,日本,他没有(资源)了就得想辙。
梁:大多数人的思维是简单的,二元,非黑即白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刺激事件,一旦触及到自己,比如发低保,他自己就是领低保的,那他首先就骂那个发低保的,因为他特别担心自己领不到低保,所以先骂出声来,看你敢不给我发么。他首先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不是心疼杨盖兰,他跟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当从心理学方面去考虑人的行为就比较明白,他一定有自己的心理诉求在里边,他就希望:千万我要领低保的时候一定给我。但又不好意思说,于是就说“一定是贪官,剥夺了她的生路”云云,他只能干这个。北京的北漂有的都比她(杨盖兰)穷,人家怎么不上吊去啊。
互联网时代高速度发展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和智商没关系,而是和认知有关系,对于一个刺激你如何认知,比如没有低保了,你是马上打工挣钱去,还是赶紧上吊去,你的认知,你的态度决定了行为,你决定你要如何应对。有的人老以为自己的贫穷都是资本家弄的,这太好了,因为还好我不是资本家,所以我穷就是因为你们太坏,一下子感觉自己所有的责任都没了,全民都没有责任感,都是社会的责任,一下都解套了,太舒服了,“贪官污吏太坏太多了,要不我早就富起来了”。
孔子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当你面对小人时你去讲义,那你一定死,人都本能的趋利避害,倾向去走阻力最小的那条路,这是必然。所有东西回到最根本的地方去讨论,可能不那么高大上了,但是能看得比较清楚了,没法掺假了。
梁:这种路径带给我们的印痕是挥之不去的,比如车,有了车100多年的文明和才有车几十年的文明在对待车和交通上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宣传什么交通文明,遵守交规,真的是宣传不进去,但是中国人到了国外往往都会明白你那套把戏你活不下去,你一定要遵守当地的规矩。最简单的一个,当你土地没有私有化的时候,你的本能就是扩展地盘,比如自家房子能不能再拆掉一点儿扩建一下,再弄大一点,因为你没有产权,而你有地契的时候你可能不会胡乱弄了,一弄就涉及到法律问题了,因为这个地等于是无主的,所以当工商发展,未来农业越来越集约化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最终一定会回归私有化,因为走不出新的路来,当代也有好处,就是社会阶层没固话,不像国外,美国等发达国家社会阶层已经固话,你想往上走那基本没戏了,那如果你有本事能突破这个阶层上去,那大家一定是佩服你的,但基本上是稳定的,乔丹也好,杰克逊也好,都是极个别,所谓“美国梦”是给这种情绪一个出口,从统计学意义上说,这种概率是极底的。
梁:揭露阴暗面不妨碍我们心向阳光。从统治的角度来说,恐惧最好使,比如南京大屠杀,几十万人老老实实的让日本鬼子杀,难道自己没有问题么?最明白的一个对照,几乎是前后脚,英国人打阿富汗死了3万人,经济怎么样,文明程度怎么样,英军死了3万人。我第一次看到京郊通州八里桥之战,曾格林沁带领亲兵和英法联军死磕了半天,被吕汉祥用火烧圆明园的镜头表演半天,结果清军死了3万人,英法联军死了3个人,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印度人,这叫打仗吗?这叫落后就要挨打吗?这不是,肯定是有些深层次的东西造成了这个问题,你可能得找枪林弹雨之外的问题,否则这个事情就很诡异,法国路易十四打算给英法联军授勋的时候,法国民众不干,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可笑的战争,你这么打没立什么功。那我们应该考虑我们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德行。
梁:我爷爷38年曾深入敌后去考察,发现有个村子,全村子的老百姓开会,推出个代表,去县城,请日本鬼子到村里建炮楼。为什么?受不了,八路军来了征一次粮,国民党一大队来征一次粮,共产党二大队来了又征一次粮,国民党二大队来了又征一次粮,没完。日本鬼子来了只征一次,他们都拿着枪,我们谁都惹不起,还是日本人来吧。你让人怎么办?你老骂他们汉奸,你让他怎么办?他不当汉奸他饿死了。当时日军的所谓炮楼里边经常只有一两个鬼子,其他的全是当地人。就是说大家没有自己的主张,这样好统治,但是也溃散得快,因为既然没有主张,那么谁牛就听谁的得了,因为他是空的,他没有自己,我祖父讲:有主见才有自己,哪怕是偏见。
3. 在谈到纪律习惯时,梁老提出西人之纪律,出于武化(集团斗争的影响),而非文化,故尔同我们习惯以为的受教育程度无关,你是否认同该观点?
4. 文章最后提出公共观念为一切公德之本,而国人向来公共观念薄弱,反观后来的集体主义精神,且不论是否矫枉过正,其对公德建设的作用亦不甚理想,试问:提高国人公德,何解?
川:我看到过一个美国的华裔家长分享的帖子,他眼里中美教育的最大差异,就是美国注重青少年体育方面的教育,他的孩子在学校里会有组织球队赛,而教练由一些孩子的父亲或祖父担当,孩子从小就学会在球队里与团队合作,类似的教育形式中国好像从没出现过,集体的合作贯彻在成长的始终,如果中国能走出这样一步,可能后代会逐渐接受或者习惯团体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