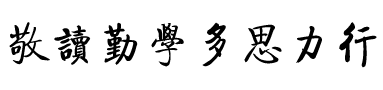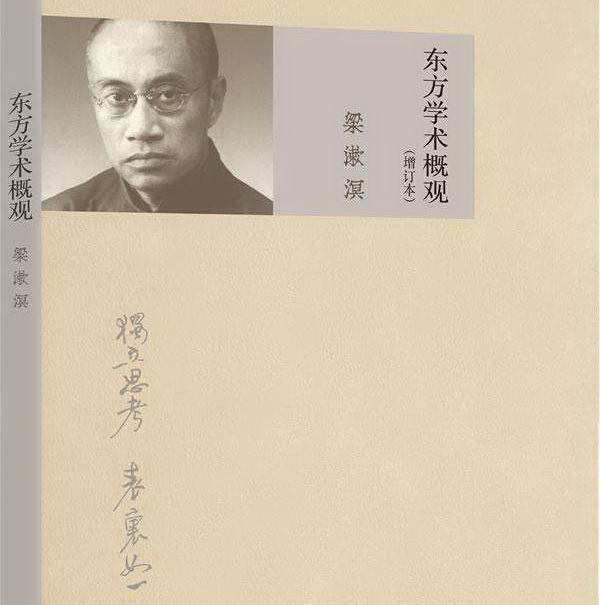第114次读书会“何谓出世”整理稿
主讲:李林溪 督导:冯蕾
读书内容:《东方学术概观-何谓出世》
李林溪:这篇文章中比如像“闷绝位”这个概念我去查了一下,是指人在奄奄一息,还有一息尚存的时候。梁老说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二执仍然还有很强的存在。文中巨赞法师和李书城先生的观点没有太多披露。梁老上一段发言的 “出世思想”,资料也不是很完备。关于“向党交心”的活动是在1957年之后,很多“有问题”的人士,都要重新做人。包括周总理都到会上先发言开展自我批评,后面才是这些人发言。
冯蕾:我这里资料记录了梁老的几次发言,梁老在第二次发言结尾的部分提到了“出世”:我一向都是出世的思想,对于马列主义在世间我对它完全承认没有抵触。但是他个人并不信奉马列主义,因为他一直信奉的是“出世”的思想。从对马列主义认还是不认的问题上提到了出世。到第三次发言,因为上回发言的原因对此大家有很多评述,所以梁老一上来就对“出世”做了解释。这本书摘录的是关于“出世”的部分。
李林溪:我个人对出世有一个比较刻板的印象,就是和仙风道骨、隐士联系在一起,脑中固定的是云雾缭绕和竹林、白衣飘飘古琴弹奏。现在这种“归隐”成为一个新潮流,如果有北清毕业,到终南山过上了出世的生活,这些很能作为标题当噱头去吸引人。
梁先生:这个我们两方面理解,我们温饱解决之后,如何寻找精神家园。当局建构的官方模板大家住进去很不舒服,大家自己寻找就会找一些“看上去像”精神家园的东西。这种情况下也能理解会出现形式大于内容的东西。首先在形式上区隔开什么24字 核心价值观。不管说稳定压倒一切,佛教还是属于当局能接受的范畴。但是联系到“藏传”,dang就立即警惕性提高了。我接触的法师说一旦跟藏地法师来往,宗教局就很关切。藏传因为本身不清楚,就具有极大吸引力。另外大家在修不动的时候,在形式、服饰、环境场所上变化让人有一种感觉,推动人的调整。这些也相对比较好办,钱花够了就行。但是真正的断二取、破二执,就是内心的功夫,很难有作为,那就只好找上师。从客体心理学来看是找到一个投射对象,一提名号好使,自己也“有荣焉”。
我记得08年去丽江,有个很有名的客栈,当时老板尚未出家。这位老板爱摇滚,在雪山音乐节认识了一个成都姑娘就离开北京到丽江开了“常春藤”客栈。一开始我去他也是很轻慢你的样子,在我朋友来回问、和我交流的情况下,就觉得对不住我,老板就来找我。和我谈完之后态度就完全转变了,开始以为是朋友所托,吃喝照顾到就行;后来就推掉很多聚会和我谈。雇了好车带我转,还带我去见他拜的上师。
我看了以后觉得这个老师不行,他开始很不解,他是那种我把家底都给你看的那种人。我和他说了我祖父对佛教的看法和老人家对这种事情的理解。他听完觉得很不同,我走的时候他就要免单,我当然不让,他说是刚从北京飞丽江,否则就跟着我回北京了。
后来他就出家了。他在修行中上师给他说的他都奉若神明,比如真善美,哪个最重要。他师父说善最重要。我说不对,首先得真,否则善就变得没有根苗了,各种欺瞒和手段都可以用。戒律里第一个就是不打妄语,如果还以善为首就不能自洽了。我跟他说不是拜上师就完了,自己的精进和修养在哪里。修养我父亲的解释就是自我的教育。现在动则加持一下,我说别,他那两把刷子,我加持他得了。
现在弄得就是形式大于内容,不过只能理解为比胡作非为灯红酒绿好吧。这里面还是有利益参合其中,比如我碰到过就是成都附近很多寺庙都是被人承包的,一年挣几百万没问题。所以不太容易弄清这里面谁是干嘛的了。
有这个机缘,很多汉传佛教的法师知悉我是梁某人的长孙就高看一眼,一定要见面或者请食斋饭之类。我接触不少一跺脚四阶乱颤的法师。那些法师之间的差别也看得非常清楚。两个女和尚,都是成都的,高下立判。一个说:这个是大补的,得多吃。另外就是:梁老这个书我读了,读了多少遍。我新修了房舍,你来就住我这,很适宜写文章。这个叫果平法师,出家前出过散文集。很有意思是她在庙里修了书舍,这个书舍是现代化建筑,完全是钢结构暴露的,里头的家具是中式的,真的有点意思。在里面组织大家读书、学佛。相貌上有区别,那个法师就是胖乎乎的,果平法师就是很清瞿,很有范儿。
佛教界里面差别就很大,自己感觉上就有不同。我有这样的机会去接触之后感觉就是不一样的。包括佛学院的博士、硕士也是天差地别什么人都有。
冯蕾: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不论国学热和为价值观寻找归宿,有不少人对于太极,禅修是有很大兴趣,作为普通人而言什么样的途径是比较靠谱的。一是说目前情况很杂乱,二来每一个渠道都是给有钱人的,变成了有钱人的生活方式。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在杂乱的情况中寻求自己的方式,第二就是我们作为平时如何去精修?我在想陶渊明写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首先是陶渊明这类人有这样的情操,就可以自我修炼了。但是更多人还是比较混沌。
李林溪:其实经济是帮助理性开发的。陶渊明算是世家,祖上是位极人臣,自己算是吃过见过,所以他能不为五斗米折腰。那些仓廪不实的人都没工夫想这个问题。有一定家底的人想到去回头看自己的人生,很多人还没工夫想呢。
全贞雪:普通人提到提高自己修为的办法,就是梁老说的断我执和法执。还有就是断我痴,我见、我慢、我碍和法执。就此来说,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上述情况,要有一个警觉。先从警觉上着手努力。现在来说警觉就已经很难得。最近老谈到“萨德”问题,我毕竟是朝鲜族,处于一个比较敏感的状态。这其中就有与生俱来的执念。别的人可以喊抵制韩国之类,很多是zf给我们灌输的理念,但情感上感觉不对。这其中有好多人要爱国啊,我的朋友圈里也有很多人觉得这样是愚蠢的。这里面怎么能分辨出来,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独立的思想。独立思想还是要从独立的人格中来。
前几天新闻也说韩国人也进入这种状态开始不喝青岛啤酒。情感上来说更容易理解,而且韩国人的行为更激进。现在国内明白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在更多接触之后,你的人格完整才有独立的思想。有独立思想才是对这些有明确的发觉,发觉之后才有破,但是具体怎么破我也不知道。
梁先生:萨德这事挺有意思,一下像是捅了马蜂窝。按理说应该抵制北朝鲜,它的反应堆离吉林更近。可见就是zf有意引导民众的情绪,让大家恨谁或者不恨谁。看了一个军科院的军人,至少说了一个比较独立的思考。萨德系统是对中国的“偷窥”,侦测范围可达2000公里,那有没有替代方案?这边别装探头,那面磨刀就任他磨吧。得站在对方立场上解决问题。这个军人提出我们、韩国、美国一起在韩国见萨德系统。解决了偷窥问题,韩国人也放心了,美国人也放心了。
冯蕾:现在的萨德系统就是美国和韩国共同研发的?
梁先生:就是布置这个系统的用处就比方说韩国只能沾5%-10%的好处,好处多数让美国鬼子占了,能方便监视我国导弹动向。
冯蕾:部署萨德真正的目标是中国?
梁先生:萨德系统雷达侦测范围能达到2000公里。
冯蕾:如果中国加入三方共建反导系统,雷达就侦测不了中国军方的动向了么?
梁先生:因为中国就在这之中,雷达控制的范围就可以调整了。韩国和朝鲜距离没多远,为监视对面违法小贩,配备一个500倍望远镜,这也是瞎扯。
冯蕾:美国和韩国力推部署萨德系统有监视中国的目的在内。
梁先生:问题是混在一起了,韩国的安全感没有解决。不部署萨德韩国自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鑫胖放四个窜天猴,韩国更有借口了,这是在帮忙呢。我们不摁鑫胖,我们又有私心,觉得他好歹是共产党人,好歹也实行社会主义,我们在打这个算盘。我们在纠结时,心理学上说叫“趋避冲突”,又有好处也有坏处这就难决策了。吃鱼又怕扎刺,到底吃不吃自己就犯难了。为了国家安全就一个办法,但为了政治正确或者政治上不孤立,这就麻烦了。六方会谈基本废掉,煤炭早几年禁运结果是否会不同,最终还是不管。现在鑫胖手里的核武器是当家最后的家底,也不会扔掉。现在看就是死局。
你家隔壁邻居弄二十个煤气罐倒着玩,他说是和另外邻居死磕,这也没辙啊。看出来谍报工作,对方搞那么多大工程居然不知道。在刚起来时没有掐死,现在人家把砸锅卖铁的工程搞出来了,现在也没辙了。
我们被意识形态带着走的时候,要出问题。不单是国家利益,官方既强调是中华民族利益最高代表者,又有意识形态上很多摆不上台面的事情,这个游戏就没法玩。在优先顺序上自己就冲突。包括我们现在要去禅修,要问清自己干嘛,是逃避,还是成长。这是最大的区别,是要逃避,到山里念念经喝喝茶去躲一会儿;还是普度众生,乘愿再来?你到底想干什么?要问到问题的关键,就是禅修都为了什么。
如果是为了成长?
梁先生:这事情就简单了,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很多上师对“供养”和“双修”感兴趣。只是包装了一下的财色而已。有个信徒跟我说过目睹情况,禅师让弟子找一个盘子让大家给红包,他看到禅师坐车里把红包里一百块拿出来塞两元的票子进去,然后叫庙里。看完之后瞬间崩溃,分分钟奔溃。
您说这个有点挂羊头卖狗肉,如果普通人真心想去提升自我,那该怎么弄?
梁先生:我祖父说得很清楚,他的佛学就是自修的。他说就是破二执断二取。
冯蕾:我在找延伸阅读时看到南怀瑾很多解读禅修的东西我都看不懂,也不知道他应该作何解,自学确实挺费劲。
梁先生:没关系,成佛有八万四千法门,律宗不行还有净土宗。净土宗就是念经,南无阿弥佗佛就是一股劲的念,这其实也有道理。走净土宗的路子就是没有杂念,用行为的办法驱逐杂念,然后纯净你的心灵。方法很多,用外科手术之类都可以,问题在于你自己想干什么。你弄得这么龌蹉在车里换钱,肯定让信众崩溃啊。法师自己也没法让弟子做这事情,这么干太累了,下回法师买车一定要贴膜厚一点的。就是吃斋放生的才做这种事。进去之后看满目疮痍,比不进去事情还大。我们都想不到还有这么玩的。我还问那个信徒说不知你师父相不相信报应。在这个过程中得看到这其中的东西,就和佛教反应的贪嗔痴又走到一起了,他不能自洽。问法师那些戒条自己能做到么?有贪嗔痴那就是挂羊头卖狗肉骗钱了。
这事情也难也不难,就是自己到底想干什么,是办个班赚几万,那就分分钟现原形。不过最起码人家愿意把钱交给他,换个别的班没人去了,我相信信众中有一开始就晕的,看着你老干这个也有明白的,这也是一种觉悟。对我们来说就是简单的日常生活。
我印象深的是03年去西藏,带团的地陪也是藏族,汉语很好,团里有人就问如何持戒,地陪说首先就是不杀生。我女儿那会儿才初中就撇嘴:贪嗔痴就捡便宜的说就不杀生。就是给自己找一个心理盾牌而已,并不是“觉悟”。佛就是“觉悟”,不是给自己找盾牌我吃肉就理直气壮了。我从来不自己杀,然后我吃。
最简单、日常最直接的就是不打妄语,要真正有所精进有所修持这不是没有机会,这就是日常功夫。
翁丽:这个“我执”、“法执”和“二取”看这个解释还是有点抽象。
梁先生:佛教的东西我的功夫也不是很够,我看完之后有一种感觉,俱生我执接近于潜意识的东西,意识解决不了。分别我执是后面有自我了才有私心,有“人亏了我赚了”的心才有分别。
翁丽:这分别就是指人-我的分别。
梁先生:这就跟宇宙不是一体的,有“大我”、“小我”之说了,我祖父觉得这个完全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说的都不对,一定要破我执。破我执就没有我,没有我就不执了,有我这事情还是个事。他给别人题字也是题“无我为大”。
有我执看问题角度会变,那几个股我都攥着,一定得涨,有偏向就是对股市看不清,心态就开始跑偏。我们用最通俗的角度去解读好像也有一个说法或者关照。弄到玄虚就是大家晕菜,就不知该怎么办了。
法执通俗说就是路径依赖,比如一个数学老师习惯用数学思维去解读,用自己擅长的领域去讲。用常识去判断这种路径依赖会对影响判断,对自己造成局限。认定某个东西好,先入为主。
翁丽:很多时候不能客观接纳别人的想法,是以自己的思维惯性解读对方的行为。
梁先生:关键在于这样就是对自己没有觉察,觉得别人都偏了。就是鼓捣大家抵制乐天这事情,dang不暗示也没人敢动。北朝鲜都过境杀人了没说抵制北朝鲜的餐馆。这基本利用义和团当枪使。如果是谁害我我就对谁狠,那不应该跟韩国起急了。我看到禁毒日宣传,就是说北朝鲜往这里贩毒,那边都没有私企,肯定是政府啊。现在都不好意思说那边政府贩毒,为什么不说?说了对谁不好,是对百姓还是官府?
就像美国特朗普一样,合适我就弄,不合适就拉倒,那倒是弄啊。那基本就是你和他谈待遇他和你说情怀,你跟他谈职位他和你谈境界。
翁丽:实际上这个法执很多时候都是故意的。
梁先生:一部分是故意。对于多数我们自觉清明的人,要警惕自己情不自禁去做这种事,我们认为我们没做,这个误差就更大了。
翁丽:那这时如何跳出来,多数时候我们是意识不到,按着自己思维惯性就接着走了。别人的感受非常不好,总觉得误解,解释不清,说话就觉得累。
梁先生:这就是你的功夫。就像全贞雪说的把脉,就得次数够,一定是大量的。包括自己就会碰壁啊。包括有点学生就是开窍快,有点就是开窍慢,悟性高低有分别。首先你无私,这事就好办,有私心又不明说,都是阶级兄弟所以对方贩毒就不提了。
翁丽:如果阅历有一些,悟性也没跟上,是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得失心。
梁先生:好像不能这么说,这里他会打算盘,没有“我”的话就没有得失了。我祖父在香港办《光明报》,准备去南洋募捐。当时民社党的一位徐老先生问他去干嘛。我祖父说是去南洋募捐。徐说不许去。我祖父问为什么。徐先生说你们民盟相当于央视,你到那里一拉赞助我这里就没法玩了。民社党也算民盟的参加成员,民盟开始的名称叫“民主社团同盟”。我祖父说为了去南洋专门做了一身纯白纯毛的西服,盔式帽,文明棍都拿好了。徐就是不让他上,我祖父一想算了,他岁数大得让着他,头等舱票也作废了。老头去了南洋,日本就攻陷那里了,老头在那呆了七年。我祖父是真的无我,并不是想我要如何,只是觉得年长得让着。必须在这个层面上他放下了。完全可以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民盟的办报经费也很紧,在所有利害得失的权衡下把什么放在前面那是他的问题。他只是说岁数大得让着,也没想到日本会攻占南洋。
翁丽:您刚提到放下,能具体说说么?
梁先生:接受这个自然的局面,今天约我咨询的小孩就是,去年十一之后就再也不找我了。靠自己抖机灵,能进海淀区前10%,也能瞬间跌出年级300名,自己想上人大附。我和她交流之后就不舒服,说我对她有负面的评价。我说你早上起床都起不来自律水平比较低,我了解到的尖子生没有自律水平低的。她觉得这是负面评价,我说没起来床是现状好不好。所以就不找我做咨询了。
我也不管,她不接纳是她的问题,我没有做错就行了。我光想我怎么把她弄来,她妈妈也着急。她母亲也是学霸级别人物,理科门清,有个问题就是觉得女儿解题方法不够先进,女儿肯定不干。这时候妈妈就有杂念,我要把我的给你。
女儿又学爸爸的抠门。太太说先生在外企工作,地点在东方新天地,加班晚饭都不吃得回家吃,而且还是被猎头公司挖过去,一般的公司也扛不住那里的租金啊。女儿就老打听梁老师咨询收多少钱,贵了就不去。母亲只能忽悠,钱都给梁老师了,不去就白给了。
在现实生活中什么人都有,不经历就看不到。她父亲还是西交大的硕士,聊着就开始破口大骂他的老板,我就明白这种人在公司混得不行。我跟他说有句话叫“命苦不能赖政府,点儿背不要怪社会”,都是别人的错是不是有点问题。他觉得自己就是老板的工具,我说那可以自己开一个。我是工科出身,一盘道儿他也就不吭声了。他太太也是中层领导,也比较明白,否则团队没法带了,觉得她先生老嫌她不做家务不对。太太加班有加班费,说雇小时工做家务也可以的,可想而知她先生是什么反应……所以太太问我还能过下去么,我回答还得看她自己的努力。这里面肯定涉及价值观的问题。
在说到思维惯性时,所谓出世间法,就是要超离所有的利害关系、算计。我祖父说宗教很重要就是站在生命之外给你支撑。人死了生命就没了,但是宗教还在,告诉你有往生、来生。支撑着你咬牙干一个事。
那些烧头香的又是另外一个事了,这里面还有盘算。用三炷香解决一个问题,省了保险费了,不用买保险,显然他的心灵上不能成长,甚至有可能出现退行。大家可以看相关的篇章,关于戒定慧,我祖父说的还是比较清晰了的。
全贞雪:我读这篇文章有个问题,梁老说到“人生的痛苦在于人生的不自在,不自主,不自由”痛苦都是因为有“自己”在里面,自在、自主都有“我”,摆脱我执能少很多痛苦。在现实生活中,例如锻炼这事,不锻炼会觉得自己是痛苦的,感觉有罪恶感。这里面也是我执的一种,有这样的痛苦是不是也是一种“不自主、不自由”的状态。那要摆脱这个状态是要不锻炼么?
梁先生:这就是我们讲的原生感觉,当你觉得要锻炼了,但一看太热了,这就开始算计了,这里就开始有分别心和得失了。当下就是饿了想吃饭,但一想这里太贵咬咬牙回家吃,这就是算计。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另说,但是如果条件允许还这么弄,而且还是常态,这就成一个执念了。我也有执念,我种过地,觉得不能浪费粮食,饭吃不了不能倒。看样子是所谓高大上,其实也把自己弄得不自在了。
冯蕾:我儿子吃饭总要剩一点,我也老说他为何不吃干净,我觉得吃干净是一个好的习惯。
梁先生:这里你看到的是现象,很有可能张昊雷就是留一个话茬让你说话。
冯蕾:故意让我骂他?
梁先生:被动攻击啊。我给你添点堵。
翁丽: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非得让他吃干净了也是一种执念,你可以让他决定吃多少。
冯蕾:这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啊。
梁先生:那是你的信念,不是他的信念。
冯蕾:那样多不环保。
梁先生:得多交流。
李纪川:我问一句,张昊雷的饭是谁给盛的?他自己盛还是你给他盛?
冯蕾:有时候自己盛,自己盛饭也是最后要给自己留点根,吃什么都一样。
全贞雪:我以前也这样,我觉得外面的碗不干净,留一块不去碰。我妈妈以前给我带饭如果觉得不好吃,就必须留点剩点儿,让她知道这个做得不好。我就是这种心理状态,我也会老剩。
梁先生:其实全贞雪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哪,不能只有一个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浪费”!
翁丽:能不能理解唯一解释就是执念,或者是其中的一种表现。
梁先生:这里就是我爷爷说的“不能强人从我”。
冯蕾:这对我们价值观冲击很大。如果真吃不了,剩下没问题,作为一种行为习惯,是不是应该把它吃干净。
梁先生:你这个太晚了,那是解放前该说的事情,一开始就跟他交流才行。
冯蕾:他小时候吃饭都吃得干干净净的,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说到这个问题你能跟大家说一下你的想法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张昊雷:就是吃不下。
全贞雪:就是眼大,感觉能吃。
潘爽:你们家谁还有这个习惯。
冯蕾:我先生没有啊,他都是扫盘子的。
全贞雪:可能是这个习惯的反叛,你们这样我就偏不。
翁丽:我觉得你这种行为就是法执。
全贞雪:就是思维习惯。
冯蕾:我一直都存在法执。
潘爽:你觉得这样他自在么?你把他的情况说给我们大家来剖析。
冯蕾:说起法执来举个例子,就说到他吃饭去了。
梁先生:她把自己的执念弄给儿子了,我觉得是得和他有个真正的交流。到底他是认知的问题:对自己饭量估计不足?那应该怎么调整,这是对局面控制的问题。我们研究人靠不靠谱,如果他对事物的评估是八九不离十的,才是靠谱。守时首先是对时间的概念评估。如果约好了时间你老不去大家就不愿意和你合作;对工作进度预估不足老跳票,对方同样也不愿和你合作,这都是自己把路越走越窄。如果仅仅是强调浪费,就是道德标签把所有问题都覆盖了,而非针对问题。我们强调是面向问题和问题的解决。
不是简单定义,比如乐天集团让出地盘给萨德系统就是坏蛋,事儿怕掉个儿,你让韩国怎么办。你家房子政府要拆,你会死磕么?乐天也是企业要挣钱,它也没违法,至于给萨德还是萨姆系统那是另外一个概念。现在就是不敢反朝鲜,不敢反美国,就和乐天没完,那也应该和萨德导弹的制造商死磕啊。
很多事情随着变化就开始变味,官方开始加以利用。厉害的看慈禧太后跟11国宣战,全世界都没有。不能说谁敢跟谁叫板就是民族英雄,要这么定义慈禧太后肯定第一名,没第二个。
不能先有一个定论就开始验证,这当然最省事。我们在这个社会里老进行道德判断,不进行事实判断。“你是坏人”,这一下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思维懒惰,以一个“坏”,什么事都好说,也说得通。问题在于这是一种认知的“幼稚化”,分出灰太狼和喜羊羊就完了,至于人物的特性、多样性什么的全部没有。
像明朝那个太监刘瑾,说要去解决军屯问题,他也觉得骂名太多,干点正事,结果捅了马蜂窝把自己蛰死了。我祖父说知耻就知道有是非了。小偷是趁家里没人来偷,偷完之后也不好意思炫耀,其实是有是非的,无非是否能自控的问题。
这里我们是仅仅有是非观念,还有没有执行力的问题。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我们容易把它弄到知识的层面,这里面深究一点“知”应该是良知,良知就是原生感觉,不是你的知识多少的问题,超厉害的原则判断是怎么样的,而非知识告诉你吃这个可以多活五分钟就来一口,在知识更高层面上去关照对生命的尊重。因为你已经吃得很撑了,因为西洋参是免费的就再来两口,这就开始乱了,贪嗔痴就开始出来了。
有时候一说出时间就飘飘然、超拔世俗,实际上不是,超拔世俗的厉害,让自己思维和心灵能平静去面对世界和自己。这才是问题所在,不是焚香弹琴大家就都如何了。这里还是有明白人。
程璐涵还在时请我参加他们高大上的读书会,去时交流时有个姓马的老板,让我印象很深,他问我,您祖父是不是推崇唯识宗。我说是。有人是看得出来的。佛教有十三宗,玄奘也是唯识宗。他觉得梁老肯定有唯识宗的功底,在这个过程里,用大量唯识宗的概念去解释很多东西。
我祖父在北大说过“唯识述义”,蔡元培先生请他去说,他自己也说自己功夫不够,希望去找欧阳竟无的大弟子吕澂先生来讲。欧阳竟无不放吕澂来,所以推荐熊十力先生来。熊十力是我祖父推荐他去支那内学院学习唯识。熊十力到北大之后就玩幺蛾子,上来就说“新唯识论”。我祖父就是担心自己说不好请熊十力来,后来请熊十力来他就说自己的,和蔡校长说很不好意思,请人来干起了这个事,蔡校长说别担心,让他讲就是了。
熊十力很狂,署名是“熊十力造”,佛祖写的书才能写造,不是著,不是编。很多佛教界的人对他很恼火,欧阳竟无老师和他打笔仗,抨击他的“新唯识论”,写“破新唯识论”。熊十力回击“破《破新唯识论》”。
熊先生理论上也是自学,从过军,湖北黄冈人。
冯蕾:南怀瑾说自己的学问主要也是自学。
梁先生:他是军校的老师。外人看南怀瑾最大的毛病就是用典用史不准,这几乎一抓一个准,这就是硬伤啊。问题是要搞校对还是看南怀瑾对问题理解的思路。我们自己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一下就这么否定了。在出世间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如何出离世间,我们能跳脱出大家运行的社会的规则,不是说我们要漠视规则。
我祖父写过“帮助理性开发的是经济”,上回逻辑思维说到破很多迷雾的办法就问“谁买单?”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先问谁买单,无主语的赞赏是没有意义的。看见谁穷给他两亿才好,说的人不出钱就这么说呗。这就是打妄语、起妄念,这没有用,给人虚幻的感觉就是我的同情心满满的,我很穷,但我的话到了。
有一回看到毕淑敏和一个在国际上做慈善的人去坐地铁。有个残疾老头堵在地铁门口乞讨,他不干了。毕淑敏一开始以为慈善界的人要捐钱,发现他去找地铁工作人员,说这老头不能这么干,不能用自身伤痛去勒索人们的情感。老头可以向有关机构求助,他堵门非常不道德。这个做慈善的有善心、原则和底线,他直接找到地铁工作人员把这人赶走。这样堵门口把自身的伤痛给人看非常不仁慈。毕淑敏说这整个也是毁三观。通常觉得人都这样了还较真,这里你如何理解和看待这个问题,有没有杂念、执念,哪个是对的,这都是具体的问题。怎么在这其中体现对人类和社会最大的善意。我们现在就是希望一个刺激一个动作,如果这样基本就不用思考,低等动物都能做到一个刺激一个动作。
这里是我们要考量的,或者说我们成长需要思考的。包括和学生的交流,就是抽象思维加工水平的高低,看不见的,在大脑里对信息水平进行处理,婴儿是无法进行的。必须个体要不断实践,在脑中抽象化再进行加工。在刚才提到毕淑敏遇到的慈善人士就是他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并非赶紧掏钱,而是想去求助相关机构,不能妨碍他人,关照的层面和深度全然不同。也不能轻易说这个慈善人士缺德,他其实做的一点也不过分,我们也碰见过那种情感勒索的乞讨。我们能不能断二执、破二取,我们要破掉那些原来认为对,其实不对的东西。
我祖父也认为佛教很好,但是救世很麻烦,太形而上了,很难实操,具体还用儒学去解决问题,佛学后面再说。我们以现在的理解能体会他说的意思。他自己说向往佛教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