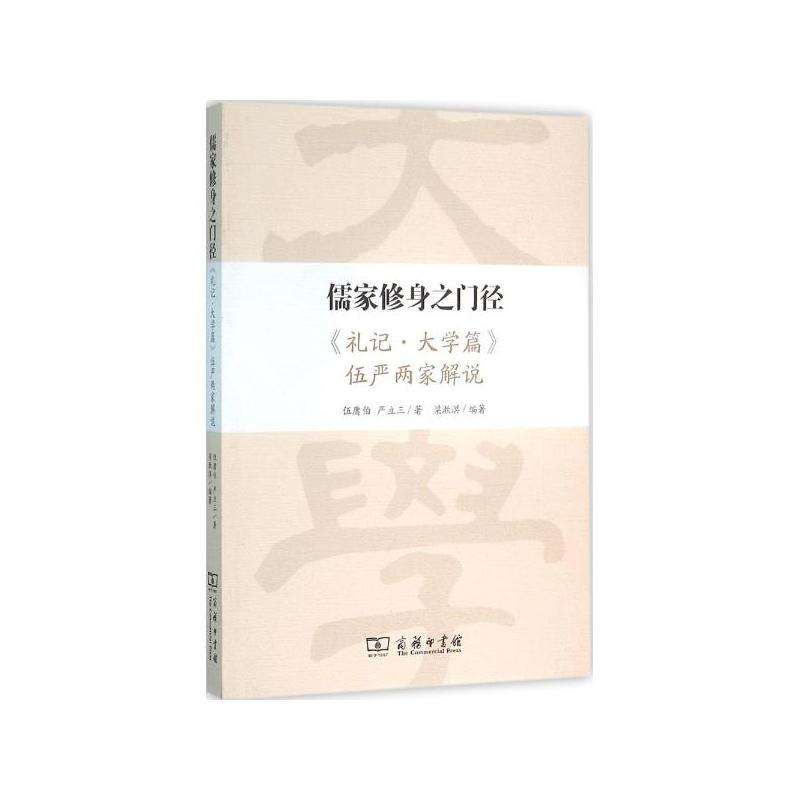第121次读书会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
主讲:耿创新。督导:冯蕾
17年10月22号
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
梁漱溟
(五)
……
《礼记•大学》一篇,昔人称为孔氏之遗书,在儒家典籍中独详著其为学门径次第,为后世言儒学者所必资取。顾自宋儒尊信表章以来,解说之者乃纷纭莫衷一是。盖在前之汉唐人但注疏书文,殊未用功体验于身心间,争论不起。宋明之世,斯学复兴,则学者究当如何用功,在彼此大体相近之中,不免人各有其所取径。朱、陆异同,其明例也。而事实上功夫取径虽在自己,却必求证古典乃有以自信而信人。此即《大学》一篇所以解说百出,独远过其他书典之由来。凡于书文讲解之歧异者总由于功夫取径之不同,且问题莫不出在所谓“格物、致知”之两句书文上,此固明白可见者。前贤如朱子、如阳明,其失在此。即今我所推重伍、严两先生,其所以立说不同,又何尝不在此邪?
须知此在事实上是无法避免的。承认此事实,有助于学术研究;不承认之,反自蔽其明。然则何独取于伍、严两先生之说?两先生于书文,不擅改古本(伍先生)或基本上未改(严先生),是即其主观造作最少;而其解释书文通顺近理之程度却最高。此一面也。更重要一面,则在其内容所示功夫道路切近平妥,有胜朱子、阳明。关于解书通顺一层请审两先生之所为说者,此可不谈。对于功夫道路问题仍须稍申浅见,以吾之推重在此。
此学功夫,我上文已自说得明白,原只在自识本心葆任勿失而已。其奈本心大不易识,从而葆任勿失的话即无从谈起。于是功夫切要便不得不转而在其如何有助于识心(或识仁)上面。凡“切近”云、“平妥”云者,举谓其于识心为切近,且妥善无病也。当前功夫道路问题在此,前贤似未有能解决此问题者。寻绎《大学》“格物致和”之文,恰似在谈功夫道路,顾其内容何指颇引起后人猜度。朱子以“即物穷理”为说,支离无当,阳明非之,伍、严两先生并皆非之,可无再赘。但阳明必以“致良知”为说,伍、严两先生并皆断其亦未为得之。我同意两先生所见。
何以阳明亦未为得邪?阳明必以“致知”为“致良知”,强古人以就我,尚非此所欲论。其所以未为得者:阳明之“致良知”实即是“自识本心,葆任勿失,以应物理事”(见前)之谓;功夫原是对的,却非有助于识心的功夫,不解决当前问题也。此试看其说“功夫不离本体”,“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功夫”,便自可见。初学之士,其何从入手邪?于是不得不时时从粗浅处指点,以资接引初学,则又易启学者冒认良知、轻于自信之弊。功夫终不得力,或教以静坐,或教以防检,又用种种方法为帮补。此严著所以有“阳明教人实无定法”之评语。而阳明之后,出其门者往往各标宗旨,别自成家,殆非无故也。
(六)
从上所述,昔贤讫未得其至近至妥之路以指教于学者,后之人顾能得之邪?此必须具体作答,即伍、严两先生为学之路是已。然两先生固有所不同。欲言其所用功夫之不同,还须从其解书不同说起。
伍先生之讲“格物致知”也,全从《大学》本文内得其训释:“格物”即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即致其“知所先后”之知。天下、国、家、身四者皆物也,而其本在身。达其本末,知所先务,一以修身为本(事事责己不责人),则心思力气一向驰骛乎外者渐得收拢来,刻刻在自身意念行动上用功夫,便自近道。《大学》提出“近道”,学者所必当着眼。明德是道;必近道焉,乃有以明明德也。由格物致知以至诚意统所谓近道。功夫要在诚意上做,而格物致知则其前提,以引入诚意者也。诚意功夫如何做?慎独、毋自欺是已。人能一念归根向里,慎于兹始,而意渐即于诚,夫然后于一向不免自欺者乃有所觉察,而进一步毋自欺焉,明德之明浸启矣。慎而曰“独”者,其始必在独居(人所不及见)独念(人所不及知)上认真,其卒也独知(阳明所云良知)炯然以露,昭昭而灵灵矣。——是谓由近道而即于道。(1)(参看我所为《礼记大学篇伍氏学说综述》一文之第六至第八各段。)
人能觉知其自欺,是其“心正”矣。从而毋自欺焉,是即修身而“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国治”、“天下平”可致也。盖凡此皆从修身立其本,而以次收其功效者。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以修身为本,而致其力于慎独;功夫门径只是如此。——此伍先生之说也。
……
思考题:
1,“格物致知”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按照伍先生的注解,当然简明切当,看上去很清晰。可是,相比来说,阳明先生多了什么?如果是按照阳明先生的注解,似乎更深刻。可是,相比来说,伍先生丢了什么?
耿创新先读主讲篇章。
耿创新:我对于“格物致知”真的是存在了很久的疑问了。我在08年跟我老师王正龙先生学习中医的时候,我老师就经常谈起“格物致知”的概念。我老师也非常推崇梁漱溟老先生,所以,《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这本书我是早就看过的。从我本心上,是非常倾向于伍先生的解说。可是为什么还没有最终确信伍先生说的就是对的?从《大学》原文来看,“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几个环节,是环环相扣,而且是平等的。而伍先生的解说,就把“格物、致知”两概念独立出来了,说“格物、致知”是理论基础,“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功夫所在。从逻辑上, 总感觉有点儿别扭。
按照我的理解,既然“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功夫,那么,“格物、致知”似乎也是功夫。阳明先生说的也有道理。
伍先生的解说和阳明先生的注解,到底取哪个,总是心里有疑惑。
冯蕾:我读了《大学》之后,理解“格物致知”不仅是在说做学问,而且更是讲做人。
先简单谈一下我的理解。感觉这句话特别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句话捉摸起来特别有味道。尤其是在现在社会,这么浮躁,一直在谈创新,在谈改革,要变,整天充斥在这样的环境里,忽然看到这样的论述,还是很有感觉。我不一定理解得对,我也感觉很大的困惑,“止,定,静,安,虑”“得”就是得到了。这和我们现在讲的变,新,很不一样。到底之间如何平衡,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的环境给我们指导,给我们引领,这个我也没想透。但是这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
然后再谈到“格物致知”,因为创新特别想探讨“格物致知”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这样一个千古疑团,我们大家可能很难通过一次读书会来讨论出来,“格物致知”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我很认同的一点就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里面其实提到了“物”和“知”。“格物、致知”到底是“格”什么“物”,“致”什么“知”,还是回到这句话去想,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这里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里其实说的是一个顺序。其实人生很多时候就是面对很多很多选择,你怎么选择,你选择什么,实际上是你内心对这些东西的排序。面对纷繁复杂的事物,如何去排序,去分前后,分始终,这个原则,我认为就是“格物”。格了物了,也就“致知”了。“知”就是“知所先后”,也就是对于自己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应该现做的,什么是应该后做的。我觉得其实归根到底,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现在面对很多选择,选择做什么,其实就是心中的格物。之后才有“诚意,正心”等。这是我的理解,抛块砖。
全贞雪:我是觉得“格物致知”确实是搞不清楚是什么。所以思考题一出来,我就有意见,历代都有这么多的争论,咱们也不是专心做这一行的。
阳明说的“良知”,我之前的理解就是人的本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朋友要掉到井里的时候,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的心都会一颤,那个就是良知。我对“良知”大概的了解就是这点。
我读这篇文章,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不知道“格物致知”究竟是什么,但是我感觉上,这个“物”是事也好,人也好,都有可能。比如研究一样东西吧,如果对象是数学,或者对象是医学,或者是什么,对其内容认认真真分类,踏下心来,把其相关内容的先后顺序排列出来,一丝不苟。研究此内容的人,只要有这种心思,对于自己来说,就不会懈怠。也就是ta说对于外物是深入研究的,那他对自己的任何事情也就是负责人的人,不会轻而易举随波逐流的。这种认真的状态,从小变大,对一个“物”,对一个“身”,对“家、国”,“平天下”是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对整个这篇文章,我大概的理解也就限于此。
冯蕾:对,我之前对于“格物”的理解,一直是从“术”的角度。我开始跟创新说,“格物致知”就是一方法论。就是你怎么样把事物进行分类。就是你掌握这门技术也好,技巧也好,道理也好,是一个方法。我在没有读《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之前是这种理解。
后来我看原文也好,看伍先生的解说也好,虽然也不是很懂,但是我发现这不仅仅局限于方法论本身,肯定还有其更深一次层的含义。
就是说,“格物致知”更重要的是“道”的层面。这里面讲了嘛,“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道”那么的高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是《大学》的“道”。伍先生讲,要想“得道”,先要“近道”。也就是说,顺着这个方法,就会首先“近道”。我感觉既然是接近“道”,应该不仅仅是器物的层面。应该还有一个更好的层面,但是这个层面到底是什么,还是不太清楚。
翁莉:我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物”和“知”之间,其实就是一个主客观的问题,是唯心还是唯物的问题。在传统的中国思想界,经常是先有自己对客观世界的一个主观认定,再用这个主观认定解读客观世界。我感觉道家基本上就是这个思路。很多中国古代哲学家,经常从自己主观认定看世界,我认为这个世界有就有,我认为没有就没有。
总结一下,这是一个世界观。先从客观实际出发,然后再总结自己的观点。不能说你先对世界有一个认知观点,再用这个你的这个观点解说客观世界。
潘爽:这篇文章我不太理解,但是“格物致知”我还是知道的。
“格物”,从字面上讲,就是把事物分成格子,也就是分类。之后分析类别间的区别于联系,加深对所研究事物的理解。然后反复分类,反复理解。
结合我工作中这些年的体会,我觉得在生活中相关度也是蛮高的。我从事的工作,不是我所学的本专业。在不断地转行,不断地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和这个方法论还是有相通之处的。在接触一个新工作的时候,先大概了解怎么回事,根据它的性质分为几个类别,这样有一个由粗到细的熟悉过程。用这个方法论,就会感觉进入任何一个行业都挺好往前推进的。
后来我又在工作中考了一个资格证,就是新业系统项目管理师,这其实和通用的项目管理资格证,国际上叫pmp,很多理论也是相通的。它里面也是讲的一个方法论,用项目管理的思路,对待工作,甚至生活,甚至教育孩子,都是这样一种思路。你要确定你的目标,先分析你的目标,之后采取那些方法。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分为那几个步骤。实现这几个步骤的时候,先提问,在思考。尤其当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去考这个资格证,对它的理解就会更多。这是我的对“格物致知”的比较浅的理解。
冯蕾:我再插一句。刚才你讲了半天,这个“格”的意思,我还有不同的理解。“格”,我以前的理解也是分类,归纳。无非就是细分和总结。但是伍先生讲的,还是不一样。
伍先生讲的“格”不是分类的意思,而是“树生长”的意思……
耿创新:顺序——树木生长的顺序。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ta的“本末”和“终始”就是一个顺序。你缕清了ta的“本末”,就知道先做什么,再做什么。
冯蕾:对,我的理解就是由这个来的。我想把“格”整明白了,后面可能就好理解了……
耿创新:朱子,和现代朱家杨伯峻,都是说“格物”就是穷究外界万事万物的道理。也可以说就是对外界事物分门别类的意思。其实这个应该不符合《大学》原理。这个梁老也经常说,我们的“理”分为(内在)“情理”和(外界)“物理”,还有“理性”和“理智”。而儒家论述的都是反观内省,是内在的践行尽性的学问,和外界的事物是两码事。你把外界的事物都“格”了,那内在的意怎么诚,心怎么正,这个不好接茬儿……
全贞雪:我是觉得这个“茬儿”是可以接上的。对外界认真的人,对自己是不会不认真的。这个在思维习惯上已经定了。所以是外界的物也无所谓,先后关系也无所谓,因果条件也无所谓,或者互相的链接也无所谓,但只要是ta 在这件事上真的认认真真地对待,只要对每个事情都深入思考的话,那ta对自己就是深入思考的。
耿创新:就是说内外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
全:对。
冯蕾:那你理解的“格物致知”是什么意思?
耿创新:等等,咱把话题再拽回来。刚才说的是朱子和杨伯峻先生对“格物致知”的解释。
阳明先生注解,“格”是“正”的意思,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就是我们接触到事物,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那有的想法是正的,有的想法是不正的。“格物”,就是要把不正的想法“格”掉,归于正的想法。那这样的解释,就会和后来的“正心”相混淆。这个“格物”不就是正心吗?
接下来就是伍先生的解释,就是这个顺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要从“诚意”到“正心”,到“修身”,到“齐家”,到“治国”,到“平天下”。
我全师姐刚才说的内外的界限不是绝对的,可是先干什么,再干什么,而后又干什么,这个顺序肯定是有的。所以“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全贞雪:那不一定啊。比如就说在现代社会,你做一件事,并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样的。很可能这个结果不是你想象得到的,不是说这个“1”,一定会导致“2”,可能这后边有很大的别的事情呢……
耿创新:师姐,是这样。可是,比如说就咱们(中医)专业来说,我们面对病人,不能说我开的这个药,它到底有没有效果,也不太知道,所以我就大概齐吧。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
全贞雪:什么叫“大概齐”,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耿创新: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精益求精,尽量把这个方子,药味呀,剂量啊,开到接近于那个理想中最对证的方子。
全贞雪:是,是想要达到理想中的状态。可是,你的所谓的“理想中的状态”,要是选错了呢?理想中的状态,就像阳明先生说的,要按“正”的状态走,可是,如果你都不清楚理想中的状态呢?你怎么知道那个是正的,那个是不正的。这个在心上论,可能还好一点。起码说你心理是平的,没有私心。但是,在事实上论,你就更不好办。
耿创新:事实上更要论。有这么多医生,医术水平是有高低的。不比别人,就我自己而言,现在临床坐诊,比以前心理踏实得多。以前老怕病人打电话,这不舒服了,那儿出症状了。我自己就那儿嘀咕,这怎么回事?总是处于担心的状态。现在心里就很坦然——当然是比以前坦然,也不是完全没问题。我自己的理解就是通过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越来越接近那个理想中的状态。当然事实上还差很远,不过比我之前要精准。
全贞雪:你所谓的坦然,可能有几种原因。一个是你对病人的病情能够理解了,可以掌控了。第二个,你这段时间的经验的积累。虽然病人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你见过。这也是坦然的原因之一。
但是你坦然了,不一定就是你真的做得正确了。你不能自己坦然了,就证明自己的路就对了,然后就一直走下去。你坦然的时候,还要有一个想法,自己走的路,要时时刻刻反省,是否真的在正确的方向上。
耿创新:师姐,我知道你的意思。扪心自问,我是一直在反省。我不敢说自己有那么大的自觉,能够时时刻刻主动反省。但是,客观上,被动反省是有的。15年就有学生跟着我临床,病人这次看是什么情况,下次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些是不光是对病人,也是对学生的交代。我经常跟病人说,效果好不是耿医生的特点,远期效果好,才是耿医生治病的特点……
全贞雪:把话再说回来,说回到“格物”上。我刚刚说的是“先后”。
耿创新:我还是感觉一定是有一个先后的。比如说佛教经常说功夫有多少层,初步的功夫怎么做,进一步的功夫怎么做,再进一步的功夫。我们看病也是,病人很虚弱的时候怎么办,稍微强一点儿了怎么办,再足一点,症状现出来的时候又怎么解。一定是有一个先后的。不能说病人说头疼,那好,上来开治疗头疼的药物。
全贞雪:不是这个一定。你是在一个过程中。我的意思和你的意思不在同一层面。在更广一点的层面上,你很难把握住,这个事物“一定”是怎么样的。可能你是想往甲处走,而ta的自身状态又在变,你绝对是要走到甲处吗?不一定啊。你认识一个事物,是有一个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有这个顺序是肯定的。但是认识之后,对这个问题的整体看法,不要局限在一定的顺序上。可能这个顺序就不是咱们能理解的一点。所以我理解“格物”不一定就是“致良知”,就是不一定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方式。这个和“蝴蝶效应”相似,一开始你看一个蝴蝶飞和遥远地方的龙卷风没有关系,可是范围广了,链接多了,这之间就有关系了。在我们目前的生活状态也好,信息沟通也好,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搞清楚,是不可能的。这里面完全有顺序吗,也不一定啊。
耿创新:但是,就像那个价值规律曲线似的。实际的价格一定是有一个大的波动。但是,长期来看,再大的波动,也是围绕着真正的价值的。我们社会上的规律,肯定是很难把握的,极难把握的。但是,从总体上看,从最初没有生命到有生命,从低等生命到高等生命到人类的出现,从这么大的趋势上看,应该是围绕着那个客观规律的。我们还是要追着那个客观规律,至少要向那个方向努力,可能做不到。比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可能做不到,但是还是要往那个方向努力。
冯蕾:所以我能理解你说的“格物”就是了解万事万物的内在的顺序的那个规律吗?
耿创新:不是。那是朱子说的,向外去找。
全贞雪:他认为是内心。
冯蕾:内心也一样啊。你就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你对“格物致知”的理解。
耿创新:我真的是很有困惑,而且是很久以来的困惑。刚好我参加读书会,这么高大上的聚会,所以我赶紧把问题拿出来,我才是抛砖引玉。
我最大的困惑是,阳明先生说“格物致知”是功夫;伍先生说“格物致知”不是功夫,是一种理论,确定这个理论之后,“诚意正心”是功夫。先生不也经常说“正心诚意”吗?我们能否“正心诚意”。这两个如何取舍,“格物致知”到底是功夫,还是理论?
全贞雪:这个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耿创新:我真不是为了学术,就是为了用,为了实践。
先生:
中国传统文化特点
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一个是冯蕾讲的,稍微有点偏,但是也很关键。她就讲中国古人对问题的了解。
中国古人对问题是凌空建构理论,不是一步一步推导。比如“天人合一”,一句话就罩到里头。你怎么解释都行。比如天子,是上天派我来的。你可以看出来,ta的容错,冗余特别大,怎么弄都能拽的通。正因为容错能力足够高,所以可以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比如你说摩尔定律,现在已经进行不下去了。下面是量子级了,再弄就该崩溃了,所以集成电路到此为止。摩尔定律可以解读到这儿(是确定的)。而中国的东西是悬空的,一下能罩到里头,所以没脾气。怎么说怎么行。有的拿《易经》讲相对论,也讲得杠杠的,相对论专家也没脾气。
就像我说的,中医说阴阳五行,一下就罩住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说的生物钟机制的问题,中医说我们早就讲了,子午流注啊。但是中医虽然能说得通,是大而笼统的,所以没法儿说因为这个去得诺贝尔奖。中医他是超现实的那么去探讨。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整体性好,因为是从山顶往下看,有没有树,可以很快看清。但是具体有几棵,长得好不好,真的就比较难了,只能走近了看。但是对趋势的把握,和对全局的了解,是很容易做到的。不是说谁高谁低,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这是一个。(先生所讲的第一部分)
格物
另外“格物”的问题我自己也曾经很头疼。因为包括阳明也讲,朱子也讲。我自己看了这本《伍严两家解说》,已经看了两遍。这个“格物致知”也是,(就像其他中国传统文化)解释的空间非常大,也可以说圆了。但是你看到极致了,看得足够多,就可以明白对错了。
之前也是咱们读书会成员杨卫曾经给过我一本书,就是她曾经非常推崇的台湾讲师尹健维,写的《论语印心》。我看完以后,感觉有很多非常好的地方。第一,和我祖父一样,强调用孔子的话解读孔子,尽量不要自己乱讲。再一个就是他用其他的经典解释《论语》,比如《易经》,比如《道德经》。就是中国文化里其他的经典,来印证《论语》。还有,看样子他下了很大功夫,就是对典籍的阅读。因为他可以信手拈来,对各种案例,对其他经典的引用,非常娴熟。还是很有学问。
但是我还是想说说他的短,两条,我不太赞成。第一条,就是他明确提出来老师高于一切。为了老师,牺牲一切,牺牲自己都是必要的。这其实和孔子的主张,相信自己,打架了。第二条,他对“天命”的解读。他讲“知天命”是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和责任。这个我觉得不太对,就是层级还是不够高。因为从我祖父这儿讲,从李泽厚先生那儿讲,还有其他的一些人讲,这个“天命”是什么?“天命”是对整个的宇宙的运行的规律的谦恭和理解。不是说你应该干什么,我应该去炸碉堡,还是堵枪眼儿,不是,这个不是“天命”。
我祖父讲,“尽天命”是你尽了力之后的那个结果。这样的话就是你生命中有大量的不确定性。所以我祖父讲得非常清楚,他有“志业”而没有“职业”。他一生追求就是两个问题的解决,“人生问题”,“中国问题”。所以他一生能干啥就干啥,教书不行就乡建,乡建不行就抗战,抗战不行就民盟,就是往前做。那你说我就死守农村不撒手,我就搞农村建设,抗战来了也不管。不是,他并不是这样。
全贞雪:那“天命”的意思是?
先生:对规律(的认知),或者说的白一点——我的解读——就是你认不认这个世界是个概率的世界。就是不可控,但是是一个高概率。随着你的理论认识越来越深刻,临床经验越来越丰富,是一个概率的提高。但是你不能说,把把赢,一定做不到,谁都做不到。所以我说你现在全面控制的结果就是对概率的不尊重。你一定要绝对不出错,这本身就是要出事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你跟着规律较劲,规律一定要反应出来。
所以这里头是个根本的问题,是层级的问题。所以“格物”是什么,朱子也好,阳明先生也好,而伍先生讲的,我个人的理解,是元认知。
一个朋友刚刚发给我的链接,我感觉很好。一个小孩儿,把《新华字典》背下来了。你说吧,哪个字,第几页,门儿清。台下就鼓掌,神童,太牛了。然后问她志向是什么。她说是成为爱因斯坦。——没有靠背书能够成为爱因斯坦的。她一格就格到那个具体东西上了。她对规律的了解,对规律的规律的了解,还是没有。那这个人还是不行。她可能能把学位拿下来,实际上还是不明就里。
刚刚我么讨论的是,你能不能把根本的规律认识清楚,把元认知拿正了。这个朋友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引用了哈耶克的话,哈耶克认为有两类不同的类型的读书人,一种是“一科的通人”,一种是“糊涂型”。一般认为大学者是“通人”。百科全书似的,但是这个不行,钻不进去,还是面儿上的东西。就像这个把《新华字典》背下来的人,那又怎样,你觉得他文学素养会很高吗?文字功夫很厉害吗?强烈怀疑。但是你没有怀疑她不认真,不去了解。
我最开始认为“格物”是一个了解,好像是。但是儒家的功夫,最关键的是反躬自省,是回到自家身上来。也就是我们对世界规律的认识的规律,你拿正了没有。你那个不正,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一个一个单开的。一旦出现新的问题,你就不能纳入到你的理解和知识体系之中,自己就不能够自洽,因不能融会贯通。然后就自己打架,就乱掉了。
哈耶克说“通人”是记忆型学者,自己就没有这种记忆力。他说如果不能把自己听到的,看到的,放入到自己的生活中,放入到自己的知识架构中,自己就永远记不住那些东西。我们不用在那些博学多才的人面前自卑,真正获得有价值的新观念新思想,能开一代先河的读书人,往往没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有所短有所长。
你博学多才,记忆很多东西,还是“向外求”,是为了让外头知道你。不是说我背这个《新华字典》,对我学习中国文化有帮助,而是我可以去秀。但是你自己想想把你闺女弄成一个《新华字典》你高兴吗,你也不高兴。尤其现在网上那么方便,可以去查。“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刚才我讲尹建维这个东西,老师高于一切,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呢。那你得死多少回?得有多少条命?就是自己不能自洽,自己说不圆。
我们要在更深的层面上自洽。不能弄了一套学说,自己跟自己打架,要了亲命了。
所以在这里头,我祖父说得非常实在,阳明学说最后就分了,大家都是自由心证。你那么说,我这么说,反正都能自圆其说。这里头就没有一个共同标准了。你讲阴阳五行,我讲八行;你说九型人格,我说大五。层出不穷,然后就是一地鸡毛,就什么也干不了了。
不管怎么讲,他是儒家学说,还是要回到自身上来。一开始我也想,是对外面的了解,那还是向外求了。“正心诚意”就没有了。“正心诚意”,比如,我重仓几个股,让我去讲股评,肯定就要出事。讲着讲着,情不自禁,潜意识里就偏了。这个不是我有意要怎么样,这对我就是一个客观存在。那让我去讲,讲着讲着就要拐弯儿。就是这样。
你能不能意识到,你在认识上,容易被自己的局限性误导。这个是你的“格物”的得要。说得白一点,尽最大可能,防止自己给自己下绊儿。这是我认为“格物”的追求。(先生所讲的第二个问题“格物”。)
致知
你能做到这样了(上文讲的格物),你就可以“致良知”了。“致良知”是什么,就是心理学讲的“原生感觉”。就是“今人乍见孺子之将入井也,皆有怵惕之心”。就是那一瞬间,就是你原生感觉。后来你一看井太深啦,救不成啦,下去我要有危险啦,那是次生的。绝对不是原生的。
你要“格得好”,像伍先生,能把自己整明白的,就一直是原生感觉。我们可能一会儿是原生的,一会儿是次生的,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
伍先生有一个很认真,又有点儿滑稽的事儿。伍先生去火车站,要晚点儿了,伍先生就不跑就不跑,然后火车就走了,伍先生就回去了。我们谁做得到,肯定跑啊。伍先生不说别的,就说自己出门晚了,这是我的问题。你看,他是这么想的。
伍先生是保定中央陆军大学第一期第一名,一个月几百大洋的军官。突然,想起来,自己为什么要当兵?想不清楚,立刻就辞职回家了。马上就没有薪水,没饭吃了。这就是跟着原生感觉走。如果是我们,就会慢慢想,慢慢想,先把卡打了,领着工资。但是伍先生一下就放下了,最后靠朋友接济他度日。
我们没有见到过阳明先生,但是我祖父我父亲见到过伍先生。在我们看来,伍先生是跟着原生感觉走(跟着良知),是纯粹的人,没有杂念。抗战胜利以后,伍先生在粤北领导的挺进纵队,两千多人,立刻交出来,回家了,不打仗了。一般人来说,至少争取一个将官当当,枪林弹雨已经过去了,要论功行赏了。他不是,哐当就放下回家了。这就是伍先生,不是嘴上说要急流勇退,然后先弄一个中将再退。他没有,马上就放下了。
伍先生去见陈炯明的时候,坦言自己刚想一枪打死他。但转念一想,这不是君子所为。结果陈炯明非常感谢他,亲自把他送出来。如果是我们的话,绝对不能把想刺杀陈的想法说出来。
这就是伍先生,服不服是你的事,伍先生就做得来。我也是孤陋寡闻,还没有听说有几个这么干的人,那就是他的功夫。他正心诚意的功夫是在那儿,不是空喷。包括你看弘一法师,去到庙里,一下就出家了。第一次妻子带孩子来没办法,但是也是口念佛号。第二次再来,让人带信儿,“此人已他去”,连面都不见了。这就是认真啊,说白了就是认真二字。
冯蕾:但是从他家庭的角度来说……
先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社会道德的问题我们另外讨论。但是他是真的,他不忽悠,这个你得承认。你说有什么社会责任,这是第二步的问题。但是他真的是说到做到,而且是想到哪儿做到哪儿。
冯蕾:顺着梁老师说的事情,我们听到那些事的时候,都会想,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家庭的责任等一堆问题。这些问题都重要,但是对你而言那个是最重要的,这个其实就是“格物”的含义。
梁先生:一个是最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正心诚意。不是利害上,这个便宜大,我要这个。圣贤是超利害的,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仅仅有厉害,这个一块五,那个八毛,我来这个。都是白拿,干嘛不拿大的呢。也“知所先后”。小偷也知道那个值钱,那个好销赃,他这么来了。
冯蕾: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梁先生:但圣贤强调的是超利害的,这是关键。考古的认为那破瓶子值钱,小偷认为那是24k的。你不能说谁对谁错。而问题他都是基于利害的考量。利害的考量是什么?是本能的考量。不是基于心灵的考量。
耿创新:本能不是出于心灵吗?
梁先生:本能是趋利避害啊,疼就躲,累了就不想动啊。
耿创新:本能是出于身体吗?
梁先生:本能就是不经过大脑,不思考。比如给你做手术,本能是疼就跑啊。但是你想清楚了,不开膛破肚就挂了。清创,疼,疼也得清。这个时候就是超越本能,反本能。
趋利避害就是本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仅仅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你不能说他是智慧的,只是算得清楚帐的人。
耿创新:本能就是局限于自己的身体的……
梁先生:就是不经过大脑的反映。是谁的我们不管,不经过大脑的,不思考。人家一忽悠你就信。或者是中央电视台说的,你就信。没有质疑,不经过大脑。
所以我们在看《思考,快与慢》的时候就能明白,系统1在工作。
所以,现在脑科学,行为科学,包括基于经济的行为研究,我自己也觉得,等于从山下爬得比较快了。把树林能够看得比较清晰了。
在以前没有先进的技术——不是科学——特别是无损探伤的技术。脑科学大跨步往前进,就是核磁,ct,脑电图,这些无损探伤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越来越逼近ta本来的面貌。
但是你从元认知上,他是不打架的。始终让自己的心灵保持开放的,不是说只有我能行,只有我全对。这样的态度你得有。如果这个没有,你再什么专家,再牛叉,也是要出事的。所以还是要回到自己这儿来。
但是你可以看,伍先生讲的ta是有步骤的。我祖父讲的非常清楚,想让你近道。最起码有一个方向。具体位置可能不清楚,但是有一个方向。可能越走越近,越走信息越多。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承不承认,我们的认知是无止境地,我们的探索是无止境地——这是一个根本。你老觉得我老背下来,你就被这个字典坠住了。
他认为脑子好使就能成为爱因斯坦,他根本不知道爱因斯坦能成功的关键在哪儿。他老是去比划。
有一个努瓦阿图人的事儿。太平洋一个小岛,二战的时候哦,美军占领了。之后就建立了一个前线机场,补给基地之类的。当地有生活着土著。打完仗之后,没什么事儿,美国撤军。麻烦了,发现努瓦阿图人多了一个信仰。拿着白纸片,画着飞机状的东西在念。
这是什么宗教啊?后来研究明白了。努瓦阿图人看起来,美军呼叫飞机,弄一块布,飞机就下来,有吃有喝,要啥有啥。努瓦阿图人一看,这比原始宗教好使,咱也弄这个。他走了,咱把这技术学到手了,咱也弄快白布招呼。
就像,说爱因斯坦脑子好使,咱也脑子好使。咱把字典背下来,咱也成为爱因斯坦。
你不能说努瓦阿图人没有学习,也不能说没有观察到。
他的认知能力在那儿的时候,他就用他的认知能力,结合他观察的现象,构建他的思维判断和行为了。你一点儿脾气也没有,你也不能嘲笑。因为他的认知局限就在那儿。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不要笑。咱们自己不要成为努瓦阿图人。你也觉得铺块布,然后就出东西了,这事儿就要命了。
这里头讲的就是一个元认知。包括对天命,我的各种体验,看得各种书籍。问题就是,你相信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个概率的。如果你不相信,觉得只要这么做一定就能成功,就遭罪去吧。因为ta就是一个不可控的世界。
潘爽:有一个说法是,只要怎么样,不一定怎么样;那如果你不怎么样,一定没希望怎么样。
先生:那就是你买彩票有中的可能。你不买彩票不带你玩儿的。
所以在这个里头,我倒是觉得看这些书。一个是在古汉语上下功夫,另一个及时思路要开阔。特别就是,西方的行为学家。而且心理学家不断地在获奖,心理学家获经济学奖。经济是什么?经济就是社会行为。而且经济这事特别直接,不能忽悠。在这个意义上,可能会低一点。我们从山上看,不容易看到底下。你从山下看,是有局限。但是他是一步一步在往前推,更直接。而且他也在一步一步不断修正自己的认知。特别是你讲元气也好,讲气血也好,分子生物学上来之后,就会提供支撑。你不能只有房柁没有房檩,没有椽子,没窗户门。你不能光有一个大框架。所以不管怎么样,这种科学探索还是在添砖加瓦。还是帮助我们人类在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明白。
所以尽管现在弄了很多烂七八糟的事,其实我不悲观,就是这个意思。只要是商品经济社会,那就让大家是傻不到哪儿去。讲经济就没事儿,安全。你可以看出来他很多东西是自己主观臆想构成的。灵光一闪,就出一个东西。
2.生活在二十一世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的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去实践两千年前的“格物致知”之学。如果有必要,我们能如何把这种所谓功夫,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之中?
耿创新:我自己看了这些说,先生也一直在说,精神要回到自家身上来。我也是一直在提醒自己反省。比如以前看病的时候,病人中途不吃药了,我就想,这病人真不识货。就老怪病人。后来我就反省是我自己医术的问题呢,还是和患者交流的问题呢?很奇怪,我也是反省,医患关系就越融洽。
在生活中也是。以前和耿敏闹了别扭,就想,你怎么这样?怎么就娶了你了?有的时候就硬提醒自己,先稳一下,先别发火。就能看到耿敏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要求,我不能把我的意志强加于她。
冯蕾:就这个问题,可能不是说我们要不要去践行,而是怎么去践行。
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基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格物致知”还是每个人对自己想法的坚持。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我自己也很多时候在打架。要不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如何坚持自己的想法。就像梁老师讲的,像伍先生,我就不管别人看法了,就坚持自己了。但是有的时候,你坚持自己的想法,能不能成功,自己也坦然接受。所谓“尽人事,听天命”。
可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旁人会说,你已经有了一定的保障了。就算是没有了这份工作,没有这个选择,生活也还过得去。就像刚才说的伍先生,从军队辞职回家,还有朋友接济,或者说还有家底儿。可是每个人的境遇是不同的,有些人可能真的只能违心地做一些无奈之举,否则会生计不保。
先生: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后来发觉不是,真的不是。就是你的行为和你的人是互动的——你也会影响你的环境。
你所有东西不断地逢迎,你最后就只能在这个圈子里头。
我记得跟大家讲过,就是那个北京出租车司机的事儿。就是对你好,你对我怎么样我都对你好。你喝酒了,胡来了,做什么我都对你好,而且不带情绪。比如说你骂了我一顿,下一个我还是好好接待。这样的结果,最后大家包他的车。所以嘎杂子琉璃球想找都找不到他。但是这个OPEN的过程他得接受。出租车司机最不可控,拉开门你知道上什么人吗?
你可以看,他的行为让他的环境变了,因为他和别人不一样。所以大家分分钟就记得他。最让人耸动的就是,一个房地产老板,包他一天车,让他去给自己办房产过户。这是信任,不是说车开得好。这不是想出来的,他就是拉活儿。这不是能想的,我这么做,那儿一个东西出来,你不要想。包括他们医生在临床上,只能全力以赴看好每一个病。不能想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你要那么看,非看砸了不可,得出人命。
所以在这里头,你的智慧能不能超越“刺激——反应”的环境。“刺激——反应”就是本能。你能不能跳得出来。你跳不出来,那你就在里边儿待着吧。这个真的是这样。你说的那个我特别理解,我觉得也是,有的时候迫不得已。你可以看韩信,他也是迫不得已。他往上走啊。
我印象特别深,柳传志有一次,碰上一个人。说柳总你看,咱俩一起起家的。我现在还是不行,碰到客户还得喝酒。柳传志讲,那就是啊,你还在那地方儿待着呢。你的买卖还要靠你喝酒卖,那你就得喝。那我这买卖做大了,我底下的人喝酒。或者根本不用喝酒,我品牌起来了。你看见了吧,不是说一杯酒都不喝。但是如果你老认为,只要不喝酒,买卖就不行,那你就喝吧,非得喝死到这上头。他也受胯下之辱,但是受了胯下之辱得爬起来。不能说受胯下之辱就受胯下之辱把,接着爬吧,那你就完蛋了。这是问题。
这就又回到刚才我讲的那个东西,就是知天命否,就是你尽力了没有。勾践也卧薪尝胆啊。你说弱,他都被俘虏了,你说弱不弱,不也给吴国干掉了吗?大清国GDP那么多呢,不想打仗,都混日子。没有目标,一让完蛋啊,不是没有资源啊。所以在这里头,有没有“知所先后”。开始也喝酒,但是得望着不喝酒上去做,把买卖做大。
这就是元认知啊。不能一下拐到沟里出不来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好,头就永远不抬了。你说你赖谁。在这个层面上,你有没有想清。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是战术的,还是战略的。你把喝酒拉买卖当企业战略来整,那你就永垂不朽了。而且你越来越印证,只要我喝酒,买卖就行。那就什么也别说了。不是说没有权变。权变是你要回来,不能一直这样。那就不叫权变了。
翁莉:有一句话就是说:终其所以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儿,而不是你和周围人。
先生:就是啊,终其所以,还是要正心诚意。我多次强调,我们认知的维度上,很容易有一个缺失,就是时间。你准备喝一年还是喝一辈子。这是不一样的。
我们老认为,买一辆奔驰是我们的初心,这个就完了。要说改善自己的出行是初心。什么事儿一具化,就不好。
所以我祖父讲,人生的意义在于无止境地向上翻新,不断地提高自己,不断地提高自己。就行了。不是我这辈子种两百万棵树,种完了找地方一跳。
所以为什么尹建维讲的天命不对,跟这个冲突了。
儒家追求的就是“人生向上”,完啦。种完树,可以做其他人生向上的事儿。不断地人生向上,一定爽。自己给自己做饭做得更好,你自己感觉也很好啊。还是要回来。你总发朋友圈是什么节奏啊。
所以修行就是日常工作,离不开生活。
所以我们自己得清楚,光把万有引力学会了,元认知不清楚,还是晕菜。
3. 伍先生解的“格物致知”,着重是要精神回到自家身上来,心放在当下,不向外逐求。而今社会,大家都在一切向钱(前)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似乎很难独善其身。并且跟随大环境的裹挟,自己早养成了向外逐求的恶习。面对这样的大环境,我们应该如何把心收拢回来,同时还能适应这个逐求的大环境,做到真正的自洽?
耿创新:第三个问题刚才也已经讨论过了。
今天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儿高大上。我自己这几年在临床上的体会。我真的不是单纯地想把“格物致知”考据出来。我们要修身养性,要用到生活中,就要先弄清楚经典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在临床上的成长真的跟解《内经》解《伤寒》分不开。我自己对经典多解出一点儿,临床上都会更灵活。有时候我都分不出,我的心得是得于临床,还是得于经典。
古人做功夫,走的路不同,也是解书解得不同嘛。
我现在用的生活中的,就是反省自我。
先生:再说一点。大家真的还是要把心放平。我们来做这样一个读书会,不是为了别的,还是为了保证我们自己不断地人生向上,这个目的不能偏颇。
伍先生也真是奇人,难得,很难得。严重被忽视,被边缘化的人。看了这么多东西书,特别是讲《论语》的书,讲孔子的书,还是我祖父讲的比较对。就是说他做这个功夫,不是说他人很牛,就是认真。认真的话,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你认真做,不认真做,就很容易拐弯儿。
特别是时时不松懈,不放松,真的是太费劲了。因为生物体有一个自我保护的功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学问,也是一个能力。我们读书会做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是要把定我们能够人生向上。
注:读书会结束,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全师姐跟我说:“我不是反对你研究这些东西,而是钻不通的时候不要较真较在上面。钻不通的时候先放一放,等以后自己知识架构到了,可能答案自己就出来了。”
联系自己学习研究中医经典的过程,我深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