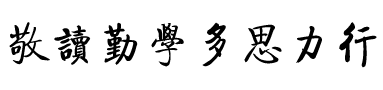主讲:曹凤娇
2015年5月19日
曹凤娇:我们来讨论思考题的第一题:回想之前的教育,多半是叫我们如何对付环境、应对他人,很少提及如何“对自己有办法”,为何梁老强调认清自己,对付自己是须臾不可放松的?对我个人而言,“自己对自己有办法”是在参加读书会之后才被开启的思路,先生也一直在强调关键是要对自己有办法,当自己有所改变的时候,你身处的世界也会随之改变。有时候会听到别人抱怨“要是环境变一下,要是别人怎么改,自己就不会这么痛苦了”,这时我能理解他正处于痛苦中,但我也会多问一句“你能做些什么来扭转局面,即使同样是换环境,如果是自己主动促成的,心理状也会不一样。”我们要扭转向外归因的思维模式,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以认清自己,试着让自己有所改变,来改变所处的环境。
杨卫: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应对考试。考试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就像数学题,只是固定的逻辑思维过程,只需要套用就可以了。但进入社会以后,面对的是活生生、多变的人,如果应对不了自己,就更不用谈和他人打交道了。前两天出院的一个病人,刚入院的时候,他就给我一种感觉——狡猾。看起来,很配合我的治疗。随着出院时间的临近,我感觉他的状态越来越不好。周一的时候,我要给他扎针,有点忙活不过来,我想着反正晚上要值夜班,那就晚上给他扎针。去给他扎针的时候,他情绪很激动:这个点来扎针了,还有什么用?谁家这么晚扎针?面对他突如其来的情绪,我有点懵,有点慌。我听完他的情绪发泄,我继续给他扎针,40分钟后,我来起针的时候,他向我道歉,讲,他因为自己的病感到懊恼、沮丧、挫败,以及对自己太太的愧疚。他的护工又讲了一句:人家针灸科就能住21天,你们怎么就只住14天?我才明白他愤怒的几个点:疾病带来的负面情绪,对住院时间的不满,还有护工的撺掇……我向他解释了住院的时间,住院的治疗,对他情绪的理解,并提出一些建议。他也认真的听了。等到第二天出院的时候,我再去看他,又感觉到他的心灵带上了坚强、无所谓的面具,我试着诚恳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没有回馈。就像这个病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面向,如果自己内心不定,就会被他带走,更不能从容应对,真实的表达自己。所以,对自己有办法才最重要。
程路涵:未交
梁先生:教育进到一个体系之后,主要的任务是知识的传承,另外就是讲所谓的科学的规律,这样的科学规律偏向机械的、严谨的,通常用数值来表达,但是我们人则是存在多种可能性的,用排列组合这种数值来计算是不可能的,在这时候人的思维习惯是喜欢简单化的,就是用简单的事情把它解释通,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但曲折复杂的解释,人倾向于选择简单的事情, 这样便于交流,也便于大家相互了解。大家喜欢在并不真的把握本质的情况下,给他一个简单,但看上去能够说得通的道理,这样大家觉得反正自己不是干这行的,差不多就行了。我之前分享过一篇文章《朝阳区为什么盛产仁波切》,上面写道“欢迎您到朝阳区来,这里提供系统的仁波切转世服务,提供加持过的喇嘛僧袍和室内晒黑业务以及后续提供源源不断的鸡汤妙文”,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滑稽了。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去理解大家向外逐求只是满足了人的低级的,不认真不郑重的生活状态,也就是散漫硬质的状态 ,这样下去很容易出现问题。但要是去认真思考,那就意味着要投入,甚至有时候会触碰到原来信念系统里的东西。在做咨询的时候,听咨询者发牢骚的过程中,我其实能听出他找到了自己问题的症结,只是在那一瞬间他没有注意,没有深入进去,或者是因为有疼痛感,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会浮于形式,不能深入内省。大家精神上虚空之后,马上要找一个东西寄托,为什么现在藏传佛教这么流行?就是大家都不太懂,于是互相就可以打哑谜,我现在有一个咨询者,85后的单亲妈妈,经常跟着师傅到处乱窜,她自己也感觉这个师傅不对劲,因为她所谓的师姐们每个都说是师傅的理论,但是她们的理论都是互相打架的。所谓的一些法师,他们也是糊涂的,当讲不清楚的时候就说你自己醒悟去吧,再讲不过去的时候,就大而化之,靠标语似的口号告诉你去忍耐,烦恼即菩提啊,化悲痛为力量啊,然后这个咨询者面对母亲的不尊重时她就忍,但忍的时候头痛耳鸣,而且还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咨询过后,这些症状就都没了,我强调的是她和母亲互动时,不能靠忍来解决问题,应该学会在不伤害母亲的情况下去表达自己的感受。这种藏传佛教的学习团体没有真正进入到人心的层面,都是大家在相互敷衍,只不过是大家抱成个团,而且一定是形式大于内容,肯定既没有忏悔也没有自新。没有自新的话,你和重要他人的互动模式还是没有改变,那局面一定发生不了新的变化。我们要理解,大部分人是不愿意深入、认真的想一个问题的,快速的迎合是容易的,真正的一点一滴的去做是难的。
程路涵:未交
梁先生:复旦大学投毒杀人事件的当事人就是这样的想法,想让对方消失。弗洛伊德的解释不是杀,而是让对方消失,小孩也是这样,当他讨厌奶奶的时候,他就想杀死奶奶,奶奶就会很痛苦,其实这个“杀”是想让其消失的意思。
杨卫:医生也经常在应付医院规定开检查赚钱和真正想帮助病人之间痛苦抉择。
梁先生: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女儿在高三高考的时候背政治,她觉得这个太痛苦了,因为厌恶而记不住,我就用了一个心理学的办法,告诉她现在让你演一个坏人,台词就是这些,你必须背下来才能上台。因为这套东西完全跟她的信念系统不相容,但是这样一假设,马上要上台需要背台词这样就好转变过来,所以一考完她立马就彻底忘了。所以我们也要理解毕福剑这件事,因为扭曲,心里想说但是央视又不允许这样说,于是到了熟人圈里就没hold住。咱们先不管对错,所谓直心是道,那就是他的道,可非要他装成别样,那他只能扭曲自己,把负面情绪压到潜意识里,他一定会迸发出来,而且这个能量一定是double 或是redouble的,最后一定会出事。回到文章上,忏悔的同时自新,自新是自我的升级换代,忏悔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是郑重,如果不郑重,比如向内归因,“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这纯粹是满口应之,根本没走心,只是一种敷衍,甚至是一个盾牌,意识是我全都揽下来了,你还好意思说我吗?使得这个问题解决不下去,忏悔真的是要起心动念,正心诚意的。
曹凤娇:我们进行下一题的讨论,学习这篇文章前,当我们“狠狠”自责时,其改正效果是怎样的?我们又会用什么方式让自己不至于太过痛苦?大家肯定都有自责的时候,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感受不同,但想必每个人都会觉得不舒服,大家是通过什么方式度过这个坎的呢?
潘爽:关于自责,我想到的是小学升初中的那次暑假,沈阳的亲戚来老家玩,然后临走时问我要不要和他们回沈阳玩儿。当时沈阳在我心目中是省会,是大城市,能过去玩当然是最开心的事情啊。那个时候,妈妈脚掌缝针不能落地,走路都是单腿拄拐。我问了妈妈我能不能去玩儿,妈妈慈祥地说去吧,我没关系的。我竟然就开心地去沈阳了。关键是,爸爸那些天出差不在家。就是说,只有妈妈一个人在家,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这些我都没有意识到。在沈阳玩儿了一个星期特别开心,然后猛然间意识到,我怎么可以把妈妈一个人丢在家里呢?于是迫不及待想要回家。可是偏偏不凑巧,丹东发洪水,交通阻塞,所有公路铁路都停运。我就在焦虑不安深深自责深深懊悔中度过了漫长的一周。这件事我自责了许久许久,那种深深自责的感觉很长一段时间都堆积在脑海里面。我觉得这种自责是于事无补的,没有改正的机会,因为我就是自私地对生病的妈妈不管不顾。能做的就是以后不让这种事情再发生。
程路涵:未交
曹凤娇:小的时候写作业,总是不能集中精力,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我就自我规定一个小时之内只认真完成作业,不能分心干别的,可我经常失败,于是常常自责,自责的受不了就诅咒自己再这样就有什么不好的后果,或者惩罚自己,但我没有自虐过啊,这过程对我来说很痛苦,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用诅咒、惩罚的方式以图改过自新。
程路涵:我在青春期的时候会将心灵上的痛苦转化成肉体的痛苦,身边很多觉得压力很大的同学也会用刀在胳膊上划印。
梁先生:从心理学来解释这个问题,这种方式能强化个体的存在感。我认为个体应该要如实的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不要去装,内外一致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我祖父之前也讲过,人在一定精神境界上被压抑了之后,动物本能的东西就强了,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贪官总是贪财好色,因为他在精神上已经完全被阉割了,包括演艺人为什么嗑药,因为他需要刺激,可别的已经刺激不起来他了。这个问题我祖父也提到过,就是机械性的问题,认为一踩油门他就应该往前走,一踩闸就应该能停下来,那怎么办?就是要刺激,但其实不是,这是“阴阳”的问题,当元气不足时光靠刺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靠平时正常的饮食起居来解决,为什么很多歌手不行,第一是透支,第二是偷偷的嗑药,来达到那种表演状态,但其实他们不知道这根本不靠刺激,而是要往回收,把欲望收回来关照自己的内心才行,这样的创造才是生命里迸发出来的,而那种状态只是一闪而过,不能持续的。崔健从来不嗑药,但是他写的东西都是有深度的,他对自己的内心有所关照,可能关照的不准,但他都回到自己的内心中来。忏悔都是竖心旁,意思就是要有所起心动念,不然的话就是敷衍,自己敷衍自己,郑重从何谈起。很多学出门道的学生,一定是她在这个过程当中琢磨了,有了自己的体会和感悟。在做高考辅导时,我做的就是降温,让他们回归到自己,神智清宁,智慧就会开始发挥作用,不用我再说什么了。
杨卫:我最近忏悔来着,也试图自新,但自新的很不成功。我不喜欢给我家里人打电话。我爸妈就觉得我和他们不亲。我忏悔,感觉这样的确很不孝顺。于是我又主动给我妈打电话。但打电话,听我妈说东说西,说的我情绪波动,最后,可能我妈也感觉到了我的情绪波动,又变成不是辣么愉快的结尾。想想,很没有办法。
程路涵:未交
梁先生:千万不要有改变他的任何想法,一定会让自己很痛苦,而对方也会很别扭。
曹凤娇:我现在和父母聊天都是在行为上关心他们,比如不要久坐,多嘱咐他们不要上当受骗,反而是我说的会比较多。
梁先生:要找到他感兴趣的点,从这入手去影响他。
曹凤娇:当读到“你自己原谅自己吧!大家也都各自原谅自己吧!”你有什么感受?当你了解“人类生命是不由自主的”,你有什么感受?为何只有到了悲悯的心境,才真能够忏悔、自新,开拓新生命?这道题源于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感受,感觉特别释然,从心底流淌出暖流流遍全身,之前痛的地方仿佛也被抚平了一些。
程路涵:未交
曹凤娇:根据先生之前讲的和潘爽分享的文章《能量的等级》 ,我认为 “悲悯”,不是一种对抗,要是诅咒、惩罚则是对抗会消耗我们的能量,当能量被分散之后,我们就不能很好的忏悔自新,我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
杨卫:悲悯心不是凭空产生的。佛家讲:轮回过患,大体就是轮回充满痛苦。以前,也接受这种讲法,但体会不深刻,不觉得众生有什么值得可怜的。但毕业工作,接触各种病人,看到病人的各种不圆满、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不圆满,自己身上的不圆满,才渐渐觉得轮回真苦,才渐渐升起对众生、对自己的悲悯之心,对世界的要求才能降低。但我也看到因为轮回过患思维的不深刻,不透彻,悲悯心也不是那么真切,很多时候,还是受外界的干扰,把悲悯心抛之脑后,愤怒、恨其不争的执念充斥于心。
程路涵:未交
梁先生: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要避免机械的看问题,把问题了解的通透才能真正准确的去共情,生出同理心,否则只是情感的触碰,居高临下的去所谓的“悲悯“,这是不行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得能感同身受,并且既要有温情,也要有决断,这个非常难,该拒绝的要明确拒绝,不要认为只要退了、忍了、让了,这个问题就能解决,这个要追溯到自己的幼年,我们跟家长pk的时候,我们只能让步,因为我们没能力跟父母较量,最后我们也会习惯于通过让步来维系一种关系,但这个完全是错觉,因为双方都是成熟行为独立的成年人,没有必要这样维系关系,有的糟糕的关系断了就是断了,断了也是你的解脱,我之前做过一个案例,案主把钱借给朋友,朋友住上大房子,可案主过的还很艰苦,一见面就想提,可一提就觉得不好意思,钱被别人借走不还,他自己还不好意思,这不是很不合逻辑吗?其实这个可以追溯到他小时候,一定是没有被平等的尊重过,借了钱就要还,这当然是天经地义的,可现在怎么要钱成不好意思的了,将近两三年都没还,这不成很滑稽的事了吗?这一定是触碰到当事人的某些情节了,我们这时候不能听解释,一定要看结果,他一定有内在的因果关系,这时候就要求我们要对人有深深的理解,不是只简单的普法,就能把钱要回来的。当你的逻辑解释不清对方的行为时,你要明白他一定有他的逻辑关系帮助他把事情做成这样,你愿意这样理解他,这本身就是一种悲悯,包容这个世界的多元性。
程路涵:未交
杨卫:想要影响、改变别人,真的很难。要自己很有智慧。有智慧接近本质,有智慧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有智慧贯彻方法。可我们,起码我自己是一个多么没有智慧的人啊!不仅没有智慧,还有很多欲望,结果越来越糟……
曹凤娇:“人原来分得出来是非”,那现今是什么让我们的好恶之心不那么清澈,从而丧失了力量呢?这个问题我很困惑,我对很多事情都没有特别鲜明的立场,往往是这样也行,那样也行,除非大是大非的事情我能清晰分辨,所以经常就是没有鲜明立场,从而缺少决断力,行动力,很难把握主动权,而且我还觉得自己在分辨不清时,就容易落于算计,没有直心是道的能力。
梁先生:我祖父专门讲过这个问题,没有主见不行,没有主见就没有学问,没有主见就没有自己,没有自己当然就没有自己的立场,他曾讲过很极端的话“哪怕是偏见也好“。问题是你对自己有没有信任感,你敢不敢把自己的立场拿出来。在计算层面判断是非是没法算的,所以还是不能落于算计,必须要超然,超然的意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不在小的、细节的方面算计吃亏,占便宜,你以为自己算清楚了,但是在大的系统下你其实是没算清楚的。在自己洞察能力不够的时候,更不能算小账。很多人在低层次中获得满足,但你不能把他赶出来,因为他是他生活的主人,你不是,你能做的就是提供给他意见,提供给他多一种可能性。在这之中,人与人之间很多观点的争执,实际上是双方视野的不同造成的,而且正因为我们的不同,这个世界在不停的前进,不管对错,但总是在不停的尝试,在这过程中倒不要求求同,但是要求存疑,特别是我祖父曾强调的”不要强人从我“。
王忆萍:很多时候发现自己存在怎样怎样都可以的时候,羡慕那些能说出自己要怎样怎样的人。我觉得这和我从小的家庭教育是有关系的,童年的很多不能说不能问在我的心里留下了窟窿。所以就有了“好恶之心不那么清澈,所以就丧失了力量的感觉。”现在社会越来越强调个体的独特性,每个人的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强,我觉得只能说去适应它,并且包容它,在不断的忏悔与自新中形成自己完善的好恶之心。
曹凤娇:感谢各位,这次读书会圆满结束,有后续问题大家可以私下进行讨论,或是写成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