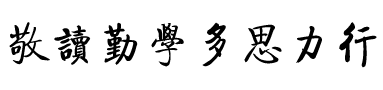主讲篇章: 《人生至理的追寻》中第五章:认识马列主义“从人类立场到无产阶级立场——读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一点心得”
时间:2019年11月23日周六中午
主讲人:李林溪
督 导:闫涵
本期读书会关键词:抽象概念、家庭、东西方差异、中距离、家哲学、区块链、凡人社会、破僵固型思维。
照片:

李林溪:我讲这篇文章其实也想到了很多,但是到时候闫涵可以补充一点,就是说大家可能对一些概念大家都知道,我们包括想举梁老那个例子,一提文化好像大家都知道,但大家理解其实又都不一样。
而且也好像大家都认为彼此好像也和自己的认识是一样的,但说出来就是说的没那么清楚。另外一点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好多抽象的概念,只有我们智人才能理解——我们总从生物的种群来看,我们叫智人——我们能从非洲走向全世界,就是通过一些这种虚幻的概念,现在流行的词叫“想象的共同体”。比如说我们是一个组织,但是这个组织其实是没有实体的东西。大家比如说这个楼是个组织,他是租的,但没这栋楼组织还在。就靠这些虚幻概念,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计划去怎么捕鹿:怎么埋伏、逗它、轰它,然后在哪把它他围住,逮着怎么分,这是一个计划,这都是很抽象的。
山子:你是读的《人类简史》吗?
李林溪:有启发,包括赫拉利他讲的对我有启发。我觉得我们对抽象概念大家都有一定认知,但你要真说出来,可能大家认知都不一样,就包括像梁老开始提到阶级立场,就是他们认为阶级立场和人类立场有不同,就包括阶级和人类这些东西都其实很虚幻、很抽象的。可能这时候说出来,大家才发现我们的认识是有不同、有差异,平常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一提一个概念好,大约我们都理解中国文化。情况就这样。所以我就提这些问题,大家任意发言。
我先说,我的从这篇文章上想到的,包括像深圳河那边(HK)的事情,特别是一些比较大的和抽象的概念,我们的理解往往差别很大。当然24字值观,理解差别就更大了,什么叫自由?可能每个人对自由的理解彼此差得非常大。
还有个我今天跟先生提到我们彼此认知的话,现在有一个趋势就越来越趋同,就叫认知上建立的墙,我只和我认知相似的人一起讨论。
但现在其实是一个更多元开放的社会,有社交媒体,大家反而会有一种这种更极端化的一个表达,现在网络上也呈现出一种对不同意见,大家都去攻击,然后被攻击了大家都觉得不好,我就跟我观点一样的人待在一块。像脸书他们也做这个算法,我们同学在美国,当时她填的就是自由主义,他们就是老推送自由主义新闻给她,其它都看不见。都会呈现出一种大家观点一致,我只看跟我认可的东西。但是现在一个我们讲的相悖的,越开放越多元反而是越孤立,大家都在自己的群体里边,就有一个向着反方向趋势,有这么一个趋势,这就是我当时读到这个和深圳河那边(HK)的一些事情给我的一些启发和想法。
梁先生:先给大家看一个东西,是稍微做了一点点的小准备,大家看一看,看完以后大家的感受是什么?
(先生拿出一张正反面分别写着“Father”和“father”的卡片)

差别在哪?一个是大写开头,一个小写开头。其实在西方文化中是什么?大写的是神父,小写的是爹。
因为这回去重庆,我是16号去的,20号才回来。就是我们不在相应文化里头,我们的感觉和洋人是不一样。一旦大写,他是另外一个感觉,宗教的那种东西就被唤起来了,不是大小写差异就完了。我想说的什么?就是我们不在相应的文化里头(frame of reference),我们的感觉洋人是不一样的,对吧?一旦大写,他是另外一个感觉,它是一种宗教的那种东西就被唤起来了。比如某人觉得是大写、小写,其实并不只是这个差异。
因为这回去的时候,廖老师想请我去重庆,我觉得可能是从3、4月份就念叨,反正她经常改日期。后来我都不敢跟重庆的朋友联系了,他们老说你提前说,我们等你,我们可以提前安排我们的日程,这弄了好几次谎报军情,我都不好意思跟人说了,都不吭声了,我说这回他不买机票我就不说了,折腾了快到年底了。然后廖老师说去吧,就买机票。
然后同时请我去以外,廖老师(廖晓义,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兼主任知名民间环保事业倡导者和活动家)还请了一个海外的华人姓杨,叫杨笑思(美国芝加哥森林湖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一同去。那个人是老三届。跟领导是一拨儿的,但是他不是工农兵学员,而是正经的参加了77年高考,大概三十四五岁去了米国,然后一直就在米国埋伏着。他讲了两个30年对他的影响,就调侃到两个30年互相不否定。因为在国内你像30多年,而且老三届跟领袖完全同岁。当时看到了介绍他的信息,一直在美国大学教书,当时我就有点先入为主,我说因为他讲家庭教育,想到时候他可能是个问题,因为我说肯定没有毫无违和感,你说你要讲理论,我也可以给你讲,要讲案例就更不用说了。然后还有我爷爷的名声加持一下就效果就更好,反观教授他可能要麻烦,学者他可能会不接地气。
到那以后,我常说很多东西,你在现实情境下,你才能破你旧有的认知,包括你可以看那个在文ge的时候就是有意思,一旦说全人类就是没有阶级立场,你政治不正确。其实你们没有感觉,我们那阵儿有感觉,你不能随便给老人让座,你是老地主吗?你得先弄清,你说地主是老的,摔地上都没关系,亲不亲阶级分。就弄成那样的一种很变态的状态,但是它是这种变态到了一种常态,你说大家都这么干,所以就毫无违和感。
所以你可以看,就我祖父一讲全人类,马上大家政治敏感。就无产阶级怎么放松阶级斗争,把什么阶级敌人都给弄没了,你看到全人类了……但是你想马克思也好,包括国际歌也好,也是强调一个全人类,但是我们就执拗在政治正确或者是给你灌输的口号里头去了,然后马上就引发了这个东西。所以它其实某种意义上等于在洗地,这是他其实老马就这么说的,对吧?但是问题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一旦被这个东西作为底层代码输入以后,它就很难去变更,可是你觉得没有必要变更,就这样,它一直就会这样下去了。
所以他就觉得动不动你一讲全人类没有阶级立场,对吧?你起来就给老人让座,他或许是老地主老资本家,可能原来的国民党反动派,想象这事情是非常的恐惧,而且很尴尬。得先问一问你是否是地主,让座的动作就越来越滑稽,成了一场政治审查。但是那阵就是把这种荒诞的东西当成一种正常的状态去延续了,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你们选的这个东西,你们的感觉其实到不强,我的感觉就马上就是那种就进入那个状态,要弄要分清阶级敌人在哪,比如万一是敌人对吧?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所以那时候马上反向的形成就是什么——越穷越光荣,对不对?所以那个《活着》就是葛优演的那个人,他太好了,幸亏赌输了,赌赢了麻烦了。弄了一个特写的就是吓尿了。然后买了他地的劳动人民直接没了,直接没了。
电影一直没有在大陆上映嘛,所以葛优的戛纳影帝一直是party有点黑白不提的那个意思。他那影片没有经过审查,直接拿出去了,就那阵把老谋子摁了好一段就不给拍片,就这么弄他,或者说给他点color to see see,在这里头也怕我们形成概念(对文ge的看法)。结果他一讲(指前面杨笑思教授),我觉得这底下听众怎么想我不知道。这回其实我觉得虽然是义务讲课——上一回去重庆给大型国企做企业培训,是两个小时,就5位数了,然后就完了——这个等等弄了4天,义务的,而且讲了绝对不止两个小时,乘5还是乘10都说不清楚(指时长)。就这么讲,但是其实也还是有收获,杨先生,因为他是两边都在(指国内和国外都待过),而且他三十几岁才过去,而且他又跟领袖一起,他插队时间更长了,我是两年整,人家是69年一直到77年。他就这更悠久,所以他对这块更了解,当然另外一个他就在西方的学术圈子里头一直呆着,然后同时有高频率地往返,所以等于两国的这种文化的差异,给他带来一个全新的思考。 而这个思考,因为他讲到了一些东西,原来只是有些朦胧的感觉,他称为学说,他已经出了很大一本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名字就叫《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他说 “那个书真的很难懂,你们不搞专业的最好别看,要不看完了,你们该骂我不该把书卖给你们”。
但是它这个东西简短截说,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什么?就是说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造成的这种差别,除了我祖父他的观察,杨先生也读过,因为他研究中国文化,所以他对《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哲学》,他也都是研读过,也都很赞同!但是他从更重要的视角,就包括刚才我们讲的“Father & father”其实就讲宗教,就是因为我们是几乎没有宗教的生活,西方就是强烈的宗教生活,所以他的生命的关节点都是都在教堂, 出生、洗礼、婚礼、葬礼,你不太可能想象,就是西方的人安排葬礼,跟宗教没有关系,或者不去教堂的,这也是很难想象的事情。那么他说这样一来以后造成了一个问题,使得家庭被弱化。我们觉得家庭太浓了,对吧?然后没有边界,然后各种的啃老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就都出来了,或者是什么把妈杀了什么之类的,诸如此类的。但是西方的这种东西它带来的影响我们也看不到。后来他讲了很多中国人对美国的很多的误解,后来我给他补充,他特别感谢,因为他毕竟还是后30年基本在美国。我说对美国的误解,其实中宣部是有巨大的贡献,就是所有的美剧过来,中宣部是要删要审,所以你看到的美剧,就像在美国做的西红柿炒鸡蛋,或者美国人做的鱼香肉丝了,这已经跟四川的鱼香肉丝不是一个事情了。这样的情况下,我说再一个就是大家要跟团去美国的比较多,美国的自由行很少,那么跟团去了以后肯定参观相对好的,也不会给你到带到什么哈莱姆区(Harlem,黑人聚居)什么的,对吧?那地方你也不敢去,旅游团也不会组织,所以你看到的所有的美国好像都比社会主义好,对吧?包括文化的这个东西旅客也看不到,因为他说他对他的一个邻居印象就感觉特别深,因为我们觉得西方特别好,教育特别好,独立性特别强,没有问题,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就说过你们想过没有,就是说独立过了怎么办?独立过头了怎么办? 我们是想象不出来的,因为我们很少有独立过头的,我都是分离不清楚的,对吧?这一家人弄得东北乱炖什么都在里头,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反正就是一锅粥,对吧?他就举了他这个邻居的例子,当时给他的感觉特别深。那么因为他在国外三十几年了,邻居孩子到了18岁,走你——18了,就被赶出去。尤其是文化,不仅仅是社会是这样,文化也是这样的。所以你也不能说你们太冷血,就是走了只能走,硬着头皮往外走,然后就这样了,就分离了以后,折腾,因为他在那住了三十几年,等这老两口挂了,挂了以后律师就通知孩子,遗嘱里遗产多少钱,什么房子地什么的都是你的。你猜他拿到遗嘱,孩子的反应是什么?破口大骂。我18岁我一文不名,你们就把往街上赶,我现在什么都有了,你又给我一大堆钱,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也没有这种体验。我觉得好都是真的,那是真的,他(孩子)说哪怕比如说你(父母)给我缓冲一下,对吧?或者比如说你借给我点或者怎么样的,或者半借半送,没有,就是一刀切。很简单,道理在哪?因为他说他们其实就某种意义上把自己的情感,把自己的心灵都搁在宗教,所以家里是没有的(情感)。
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就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一个概念,我觉得对我们启发其实很大,但是对这个概念的划分以及利弊,我跟他理解有差别,或者是有点争执。他就他说其实我们一定要明白,中国人的优势在小距离里头,熟人社会,对吧?都姓张,有张家村,或者都姓王,王家屯,你看见没有?就这里头我们整得特明白,对吧?那个是堂婶,那是表姑,你看有没有?对吧?大家学过英文,他没这么多折腾,为什么?他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教堂,放在宗教了,他没有那么多功夫折腾这些事儿。
另外一个我以前也讲过,大家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上帝之子,所以即便是老爷爷也是被直呼其名,对吧?也没有所谓的长幼尊卑,因为我们的尊卑都在上头。他说其实你去到西方去排,你当爹的你得排在第3位,假设太太能让你往前排的话,对不对?大写(Father)的已经排到爹前头了,上头还有一个圣父呢,看见了吧?圣父、神父、爹,爹就进入前三名而已。这还太太如果不干,你还进不了前三名。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不在美国长年生活的人,你感受不到它的那里头的所谓的好与坏。所谓相应的,正因为这样,他是教会成了一个中距离关系,所以你可以看,他说洋人的中距离关系就特别好,对吧?同事之间、同学之间怎么处,都是边界非常清楚的、有条不紊的。
我们因为缺少(中距离),所以我们就觉得他的中距离是它的全社会,其实它底下根本就没有的。他的近距离是没有的!有也是那种凤毛麟角,是家族,比如交通不便,只能是一个熟人社会。如果高流动,然后在美国那种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的那种文化的影响肯定是不太注重家庭!他说但是问题就是说,因为你在家庭里,包括我爷爷,当然他是因为他没在美国或者西方社会生活过,他说我特别佩服你祖父的敏锐的觉察,他没在国外生活过,但他一眼就把这个问题给看出来了,“没有宗教的生活和这里头重人情”(指中国)。
因为美国都是中距离,中距离就是本来我就跟你没啥关系,对不对?顶多是一个教区的而已。对吧?好,所有的都是那种,我们老说中国人公德不行,私德行。其实不是,你看杨先生的主张,他其实把这个名义给你破了,近距离,有很多的叫法则也好,或者叫称谓也罢,可见他是很认真的去解决他,因为注意力在这儿对不对?相应的就中距离的这块我们反而不行,而且我们往往比如说容易用家的东西往单位带,然后这个事就出麻烦了,我把你当家里人,你怎么跟我这样?包括我们也都遇到过,比如我跟潘爽也讲过借款要打借条,我们觉得不是一家人还能弄这个吗?但是其实你看美国人绝对不会,因为一刀就切在那儿走你(满18岁离家的例子)。然后你可以看西方人研究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中距离关系。
又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没有这种中距离关系,然后我们要进入这种关系,比如说不管是公司还是一种社会团体去工作,我们这就是仁义道德,仁义礼智信,你就发现不好玩,就行不通,对吧?你在那没法弄,对不对?相应的比如西方的这种东西:不要打听对方工资,不要打听人家,什么属相不要说,人家宗教都不要打听,这是洋人了,中国人一定问你怎么了,结婚了没?(怀了)几个月了?你在外企你去试试,人肯定说你脑子进水了吧?
所以他的解读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底下他已经讲了很多的哲学,我们也不太懂。但是后头他继续让我有一些新的收获,我觉得虽然是义务也还值了,汽车压罗锅——死也直了。
因为我想想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告诉我你们的原生感觉是什么?听到这些东西。康德、洛克、笛卡尔、柏拉图,你们的第一联想是什么?
众人:哲学、西方……
梁先生:还有呢
众人:理性
梁先生:对吧?都是大咖对吧?或者看过的书,或者看过金句,然后杨先生总结,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共同点是啥?除了理性。
潘潘:他们是一个理论体系的?
梁先生:嗯,都是希腊的那种逻辑。跟日常有关的呢?他们都是光棍,你知道吗?都是光棍,所以他们都是光棍,他们肯定对家庭没感觉。所以他们对家的态度基本上是负面和否定。所以你看他们对家庭的评价,就这些大咖你去找、去看。但是它又是绝对的、西方主流的,比如说逻辑和哲学思考的,对吧?就肯定是毋庸置疑的那种权威地位。我们也学了一些哲学,但是老师从来不讲这些,全是光棍。
全贞雪:这是新的思路。
梁先生:对吧?但是问题就是存在决定意识。我觉得很开脑洞,所以他自己说儒家儒家,没有家就没有儒。其实也对,因为他所有的东西,他关于人伦的他一定是基于家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西方人讲的是“国家”,中国人讲的是“家国”,对吧?中国人讲是家国情怀,而且中国人骂人骂得狠说什么?没有家教,可不是说你没念过书,他比如说你不识字,这个都没有攻击力,也没有贬义,对吧?那也就说反映出来中国的家庭,它的功能跟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对吧?一旦说你没有家教对吧?你比方说你海归博士什么都不好使,就彻底的从根儿上就给你否了,你啥都不会。
所以在这个里头他肯定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因为他在美国的这几十年,肯定他还是琢磨过了,而且他自己号称,比如他跟美国哲学学会的主席发电邮,就说这个问题,美国人也承认这方面他好像很少在这方面去关注,那么我们现在特别是以武志红为代表的,对吧?还有网上的就是父母皆祸害,对吧?人生家庭是万恶的渊源。
李林溪:豆瓣都出小组了……
梁先生:对吧?但是其实我想说的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它是一体两面,它既是问题的根源,也是幸福的来源,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感觉到好的,他也是来自家庭,感觉到糟的也是来自于家庭。但他说洋人把家给弄没了,你把它画一个图,就是大的一个大枣核儿,其中一极“近关系”就很少,中距离的关系很大。你知道吧?然后再有就是你挂了以后,然后你跟圣父就有关系了。
但是我们因为缺这一块,我们的中距离肯定是有问题,因为它不是工商社会,对吧?然后又没有那么强的宗教势力,然后我们就觉得特别是因为我们因为没有猛然的一进入社会,刚刚毕业,觉得好多东西都不对劲,因为你即便是同学关系,但是它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有没有利害冲突,又是朝夕相处的一种关系,所以那个关系其实也是很近的一种关系。和你上班的那些人,特别是你在外企去工作的是完全不一样,他衔接起来还是蛮吃力的,还得这么着,不能那样了。有各种的需要学习的部分,然后我们觉得特别欠缺,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西方文化好好,就是要学习,就是要独立就是什么的。但是其实我们非常清楚,所有的独立的基础一定是跟母亲建立了好的依恋才去完成。而这个东西分离,包括独立,它其实又是跟我说的,就跟他长牙似的,对吧?你不能闺女掐着表,你怎么知道老师讲了13个月长全,你怎么还没长全,你要追究责任。
潘潘:我们讲小孩三翻六坐,然后全家人都崩溃了:3个月怎么还没翻?6个月怎么还的没爬,有问题吗?都在那里可焦虑了。
梁先生:对吧?它是一个轮廓的,不能掐着秒对小朋友要求。所以这个里头它没有弹性,他也出问题。回过来,也不是说我们都特别有柔性。但其实你可以看,特别是你可以看大家学过法律或者了解一些法律知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海洋法系比大陆法系的柔韧性好的多。对吗?它判例的时候,就可以不断的升级迭代。
然后我们法系这块就很痛苦,而且有时候弄着弄着就开始打架了,把自己弄沟里了。所以那时候我们老调侃美国怎么法律什么很荒诞的,其实他就什么他是没有案例,对吧?因为这个事一直比如说没有处理过这方面的,然后他处理到了,然后再怎么弄。包括廖老师就讲在美国也做过几年访学,然后看一群小朋友,说是幼儿园阿姨带着她上去就摸人家脸,然后立刻就被制止。(被质疑)你要干什么?离开他多少米要不我报警了!老奶奶觉得好可爱的来摸一下,这个都是不被允许的,就是你不尊重。廖老师就很感慨,后来我说我能理解你,但是反回来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孩子她喜欢被你摸吗?比如她要看你很慈祥,她愿意跟你有肢体接触。而我们不管,比如让阿姨亲一下……妈妈抱完了以后给姥姥抱,小孩愿不愿意我们不管。所以这个里头他都是混淆在一起,其实后来衍生出一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再婚家庭,然后两口子都DIY嘛,在地下车库还是地下室,刷家具还是刷什么,反正弄很热,就俩人都光着膀子在那干,无所谓就干活嘛,而且是有地下室吗?然后干完了活就上来了。上来了,这还有孩子,有亲生的孩子,有前面的孩子(组建家庭前的),自己亲生的孩子然后妈妈就说正好是个机会,要认识人体,男性身体怎么不一样,还讲了一通很科学,就完了。没多久,过了一段,警察叔叔来找他来了。因为什么?就是他的几个继子当成一个很幸福的故事转告给跟生母,生母说这个不行,这不像话你知道吧?然后报警。
众人:哈哈哈
梁先生:你知道吧?然后就打官司,来回打,而且也是判例什么折腾半天,然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反正就是扯了半天,最后反正好像而且州法院和最高法院还不太一样,但是意思最后还是好像是折中了,警告说这个不合适。 因为还有不是你亲生的,另外一个年龄是不是合适,你有没有征求意见各种的,反正总之不是一个这么着不是个正常的教育方法。你热了光着膀子,然后就来这么一家伙,对吧?比如说我们今天讲一讲,不是那种形式,你知道吗?中国人第一肯定不讲,也不会光着膀子。
然后后头还有类似的官司,就由牵一发开始动全身,就是动孩子,就摸孩子的问题,你知道吧?这个摸孩子也有类似的。就这么怎么样,最后他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不能碰,有的时候可碰以,反正怎么样,然后有人说接触是必要的,最后最高法裁定就是不能碰。
为什么?如果你法律上开了先例可以碰,如果有猥亵儿童的怎么办?因为你说可以碰。因为他法条的制定必须得考虑所有情况,奶奶摸一下是那一下可能没事,但是如果有事儿,恋童的怎么办?因为是法条得有更广阔的适用范围。所以我自己想说的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跟我们讲这篇文章,他在那个场景里头,对问题的观察和体验,是我们在这怎么看美剧,怎么去美国旅游,你都得不到的那种认知和看法。
因为我们觉得独立是我们最大的焦虑,因为老独立不了。对吧?那边觉得怎么那么冷血,直接到18岁掐着表撵人走。他是这么一个反差,所以后来我觉得我说挺好玩,这种东西其实不是我预想的,我预想可能就是培训讲课,然后义务就义务了,反正答应了廖老师,约好的就要把它干到底就是了,反正就这么弄。这个东西他会带给你很多的启发。当然杨老师老觉得依恋不够,肯定在美国家庭看到的什么?依恋不够。在国内看的就独立不够,你不能说哪个人就是对、哪个人不对,但是他的中距离的文化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包括像西方的,他向外逐求它就是“有对”的,这样的话他的中距离关系都是“有对”的:咱俩就是同事。对不对?到此拉倒完了,没有必要再深交,即便有必要,一定是私交,和这个中距离已经没有关系了。说我愿意我走了以后,我还留一个联系方式,将来或者我到了一个新的公司,我告诉你小全,我现在在哪上班……他是这么一个事,完全是私交。
但是在这种所谓的公开的所谓公德部分,他一定是没有的,也就到此为止。所以这个东西它和一个工商业社会的运行的需求,他会满足这个。但是我们工商业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进入到社会生活,当然这个东西就不一样。所以其实我原来的感觉就是他没有讲这个的时候,我其实已经跟大家可能或多或少说过,就是说儒家东西在家里头好使,出去了好像不行,不能按这个弄,但是没有宗教,中距离这些东西没想到,但是我替大家想一想,我们读书会我记大概提过这个问题,但是他这样一弄,他把它上升一个哲学的角度去看,显然我再给大家转述的时候,我想想大家肯定有或多或少的共鸣或有点那种开脑洞,还有这么玩的。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吧?始终保持警醒,教授在那上头讲,容易群情激奋,后来廖老师都踩他的刹车,比如太冷血了什么的。我说他两个问题,他在中国的家文化成长起来,然后到了美国就那个东西完全不入流了,他的那种被压抑的感受,对吧?还有他的这套东西,因为洋人根本就不感兴趣,所以包括他的学说可能还没有,比如说一坐1000多人,听他讲,他都找不到这么多人,你知道吧?所以他到那个时候他就很带感,越说越愤怒,越讲越激动,然后就怎么样,西方都忘了这些,我说不能这么讲,真的不能。
因为他里头肯定有,特别是我说你这么讲了以后,就底下特别是家长来听,他就觉得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对吧?因为他们家孩子都赖得都不行了,你还说不能让他过早独立,他现在是他根本不独立的问题。对吧?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就是各种的立场和体验不一样,而且特别是对中国家长这一块,他怎么能够把它弄清楚,父母都发愁呢,小孩基本就是赖在父母身上的,这样孩子都处理不完,你还说过早独立很可怕,他肯定不听。所以在这个里头我自己的感觉就非常深,就是他的情绪讲讲他就非常的激动。
通过这个过程自己去感觉,通过我去讲以后,希望大家也通过这种思路,很多东西不是我们可能我们必须要学的,或者我们怎么要学的,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这么一讲,大家对所谓的家哲学有一个了解了,你同样的也会给你一个新的视角。我说我就跟杨老师说,我说显然就是中国的中距离的肯定是一定要补够,因为大家很多他要走向社会对吧?你不走向社会,或者你在家里完全不做准备,最后他要出问题,而且因为由于边界不清,最后就酿成血海深仇都有,因为我借你几块钱几万块钱,因为没打借条,然后我就真的忘了,然后你那边就真的愤怒,对吧?原来可能是亲兄妹,现在就弄的简直就是你当哥怎么那么狠,甚至不吐人骨头什么这种东西就出来,因为它解决不了。
所以我说显然其实就一个边界在哪的问题,边界就是在于就涉及到钱财了的时候,还是要走契约。情谊上没有关系对吧?你忙行你们家那花,我到时候帮你交,把钥匙撂到这,我去这都没问题。中国人这都好说,对不对?但是涉及到重大的钱财的时候,还是要走契约。防小人不防君子,君子肯定他会还钱,但是你要有这个东西他就好办了。所以在这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也正好是中国最传统的哲学思想,就是说阴阳互根:家给你带来幸福感,家也会造成问题。这都是一体两面。
李林溪:我是想到原来先生也讲过梁老一个观点——《论语》往粗浅了讲,现在好多观点都一下提得很高,然后大家的理解就是往玄学上探讨,比如说像马克思好多东西,好像大家一说,本来马克思那些他写的我看过一下,就说什么法国革命,确实他引用的东西又多,我们又没有文化背景,好多那种比喻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看你就会觉得确实很高深,然后一探讨反正也不往接地气的方向说。大家反正都是玄之又玄,空对空这么讲,我就担心好多概念,我们都提大概念了,就应该往粗浅了讲,有些东西可能才是会对实际生活更有指导,你光那么反正都讲大词来去压倒人家,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闫涵:林溪有提到说这些抽象的概念,但凡是这些抽象的概念乱七八糟背后总觉得可能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你们谁搞明白了这个区块链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怎么运行的?为啥突然间就变成国家的战略了?有没有人能说几句?
潘潘:我最早看比较通俗的区块链的解释,就是两个人谈恋爱,然后男生说我会爱你一生一世,只在以前只是他们俩的事。然后有了区块链之后,男生说,我爱你一生一世,七大姑八大姨,所有同学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然后所以他们在恋爱过程中说的所有的话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有一天他们要分手,他说我不爱你了。女生说你曾经说过,以前男生可以不认,但这个时候全世界人民都出来作证,说你说过这话,这就区块链。客观的会把所有的事情去记录下来,然后这种客观性是被所有人认同的,被这种实时地记录下来,然后有不可篡改性。所以我一直我没有仔细看,我也没太清楚,因为区块链之前在我们业务里边我们也有多少提到,因为讲追溯。最早政府也想投钱做追溯,后来政府说很难做,因为政府建了这个平台,企业不愿意用,企业说我凭什么把我们的数据放上来,所以只能是先从大企业,像这种蒙牛伊利像大的奶粉企业,哈尔滨制药厂等大型企业,它自己本身有自己的质量管理体系,他说我要建立这种追溯,我才能保证我企业这种信用,但是对于那种中小型企业,它就很难把追溯体系建起来。但是理想的状态就有,如果大家都认同区块链这个技术,我在生产过程中,我把我所有的生产信息、流通信息我都记录下来,那么我在任何一个过程中,我的信息都是可以去查找的,可以去证明他的产品的真实有效性的,就是可以避免这种假冒伪劣,然后再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快速的追根溯源,是想往这方面应用,但是我们也没有落地的东西,因为还是挺遥远,反正政府讲我们也跟着炒,我们方案里面也会提,但是其实从技术角度上我也没有十分理解,只是大概了解几分。
李林溪:我今天上午去世界5G大会来着,最后一天,现在各种运营商这种5G的应用,有刚刚提到就是说的边缘计算,说现在有5G支撑网络大数据,然后这边好像说的刚说去中心化,就所有的比方说好多的信息,有些原来都是到中心去进行,比方说计算或者是进行处理,现在是从分到各个点同时可以进行计算。但是区块链是什么?我不懂。
闫涵:不仅仅你们没有把这个东西弄明白,我毕竟搞IT出身的,我也是越看越糊涂。然后我这两天就在不断的挖相关的信息,越挖我越糊涂,因为这个区块链的东西是一个Anarchism、反中心主义、反监管主义者提出来的,那就怪了,按说这玩意儿你说在西方去实施,似乎才正常,咋就变成我们的国家战略,然后我就这两天脑子里面就很乱,我就想不通,就不断地在翻查各种各样的文章,我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的思考。
区块链技术其实就是信任的中介,是传递信任的一种思维和技术模式,说到区块链就必须要从比特币做说起,比特币的创建者中本聪(当然这是一个假的名字,这个人到底是谁?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一直是个谜)是为了创造比特币才去开发了这样一个区块链的应用,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称呼比特币为区块链1.0,比特币就是为了实现去中心化的价值传递,在价值传递方面人类从一开始用牛羊贝壳(无中心)、后面用金银、银票、钞票、用信用卡、支付宝(都是有中心的),我们现在都是以中心化的第三方以及中央银行在守护和传递这份信任,而比特币的诞生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不用再相信任何第三方,不用再相信央行、国家,而是我们开始相信一个公开数学的算法。
这个说起来有点抽象,我举例说一下比特币的运行规则,比如说我想给山子转账一个比特币,我第一步要干嘛?我是要在网上进行广播,我要告诉大家,我要给山子转钱了,我要转一个比特币。这个广播当中包含了我的比特币的公开密钥和我要转让给山子的信息等信息,网上会有无数台电脑收到我的广播,而且这些电脑上全部都存储一个最新版本的相同的总记账本,比如说师姐的电脑收到了我的广播,先生的电脑也收到了,潘爽的电脑也收到了,问题是怎么判断我这条转账信息是真是假呢?
那就是它使用了一个数学加密的算法,通过这个计算2的32次方次(42亿次),最终的目的是找到那个小于目标值的字符串,而这个过程因为都是穷举随机运算,这取决于计算这些数值电脑的运算能力,当然因为是随机的,所以运气也是关键,很可能潘潘的电脑很老,但是偏巧循环计算的随机穷举过程中就运气好,先计算出了这个符合要求的结果,然后就会向附近的网络节点传播我已经计算出来了,那么潘潘的电脑就有了新区块的记录权利,因为这个区块是包含了上一个区块的字符串数据和生成的时间数据,所以其它后计算出来的电脑根据比对就可以知道谁是最先计算出来的,换句话说区块链的计算是同时重复运算,消耗大量的电力和运算资源, 这就是为何很多人批评区块链非常的浪费和低效。
那么实际上大家听到的区块链并不是我说的这种,而是最近几年西方社会组织和金融机构继续在改造区块链,比如美国Facebook,它在推动的是由一大堆的金融机构,但是不包含银行,因为他们要颠覆的就是银行的生命,所以的话一大堆金融机构跟他合作去做了一个电子的加密货币,叫Libra,但是注意这个就不是第一代的区块链了,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区块链2.0(只是为了区分不同,并非版本的升级,实际上可能是降级),也有很多人称之为联盟区块链,那么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因为1.0版本的太浪费资源,效率太低,每10分钟才能生成一个区块链,每个交易真正被确认需要1小时时间,这太低效了,所以他们就想是不是可以让一批有公信力的组织和机构一起成立一个多中心的新区块链系统,注意,这里不是去中心化了,是多中心化,比如100家机构,每家都有一台高档服务器参与竞争记账权利的运算,然后因为大家彼此有竞争关系,并且都是大品牌,老百姓相信你们,同时又不是政府部门监管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可以极大限度的减少运算量,又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信任问题,到这里其实已经和1.0版本的初衷完全改变了。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问题,我刚才也在问,怎么现在突然这个东西就发展成为我们的国家战略了呢?美国可没宣布要把区块链当做国家战略啊,那么到了我们国家,现在的区块链我这里称呼它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块链,为啥这么说,这个阶段的区块链我们可以称之为3.0版本,也有人称为私有区块链,它不再只是记账形态和内容不再仅限于货币,而是可以将任何虚拟无形资产和数据的所有权进行多点登记,实际上如果真的可以基于相对可信的区块链系统去实施这个技术,那么未来我们的生活的确可以更加便捷,你比如说以后如果用了这个东西的话,我去政府办事,我再不用证明“我妈是我妈”的问题了,对不对?我就直接给他一个字符串,那就告诉他,这就是我所有的亲人的这部分的信息,你在系统里面验证一下,验证是正确的。就按照刚才说的复杂的计算模式算出来那个数值是符合要求的,那就可以证明了。或者是我们在换工作的时候,如果我证明过去我所有的履历是真的,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应用领域,比如你要去交易一个数字资产或者是无形资产,比如说你的一个想法或者创意,你可以卖掉它的话,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证明最后的所有权。尤其是像现在的中国,比如好像对一周以前,我妹妹在日本就被一个中国的骗子骗了16,800,在微信上被骗到,具体的东西我先不分享,但是我只是说我们中国大陆现在就是假货、假消息、骗子横行的这么一个地方,如果有这么一个很美妙很美好的一个解决方法能够出来的话,其实挺好的,但是我为啥说这个我们作为国家战略的区块链叫中国特色的区块链呢,就是发展到我们这里,不仅仅要有中心,而是关键还要有Goverment监管,换句话说偶们的Goverment要在虚拟数字化的领域控制数字“主权”,控制自己的监管权,但是问题就是这个是一个悖论,本来信任建立在数学算法和竞争记账的非人为机制上,现在又中心化了,又要监管了,这里到底整出来的东西到底是谁相信的可就难说了,我的判断是Goverment可能是希望借助这个思维来解决自己内部跨部门的信息的准确性和价值转移的可控性,但是这个最终可能是一个四不像的东西,换句话说,发展到我们这里,区块链的初始精神早已被彻底剥离,留下的只是一个抽象概念的外衣。
李林溪:闫涵你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我脑袋嘎嘎作响跟不上的速度。
闫涵:因为我前面这部分的资料我挖了两天,我真的是越看越糊涂,因为涉及到里面有些技术的东西的话,我原本学过技术,我为啥看不懂,后面我就不断的去找,包括经济学人上的资料,包括国外的一些资料。这个东西没那么复杂,每个人都是通过对区块链的应用的角度去解读这个技术,每个人都说的都对,也都错,这个东西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思维,关键取决于什么人用他,还有这个规则是谁制定以及怎么制定,到底这个东西能创造美好还是创造邪恶?点就在这儿。
梁先生:其实我的感觉是这样,最近我在看一本书,这本书大概现在我记不清是哪年买的,但是这本书的发行日期是07年, 2007年。结果因为就扔在那了。书也不厚,终于想起来去看了。那时候一看结果那里头就在讲蓝海。07年,12年前在讲蓝海,但是他其实讲的是健康管理的书,这是一。再一个就在那里头他也讲西方的医学,他也是在西方医学院毕业,然后他又在英国伦敦拿的针灸师的执照。他有句话我觉得讲的很生动,他说西方的医生关注的是什么?我们原来就是认为关注它健不健康?也对,但是他说的是什么?他说他关注的是个体的健康状况,对吧?这个试表完了的状况,这些指标对吧?在瞬间的状况,这不是一个连绵的过程,它是一个状况,是在线的。就这张片子照完了或者心电图出来了,是这个状况,它的治疗手段是针对这个状况的。
全贞雪:可是真正中医说的是中医是有时间段的,辨证论治也是状况。
梁先生:时间可能是不是西医是不是更短?比如上泵或者上什么就马上采取措施对吧?特别是ICU,你可以看得最清楚,马上处理,立刻反馈就出来了嘛。再有一个关于dang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清楚,很多的时候,我们想的dang和他实际的dang中央,它不是一回事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91年,我去中南海的经历,91年我去中南海,我怎么去的?我骑自行车去的,因为那阵没有那么多的车,对吧?骑车去的,而且那阵更卡哇伊的是什么?还没身份证都是工作证。你知道吧?然后我,对吧,因为有一个朋友在里头工作,原来就是认得,很熟悉,也是学陶瓷专业的,后来这老先生不知道怎么折腾去中南海上班了,就在袁牧手下。然后他就说要进行国务院研究室要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要开个座谈会,他说我这正好需要一个科学界代表,我说我也不能代表科学界。他说你这个年龄最好,我说我们其他的都有代表,我说我也不去找了,你就来,我说那怎么去,他说你骑车来就行了,我说好。也没多想骑车就去了。是从老的国图北海那边进去,我也当时就想骑着车看解放军拦不拦我,就一直没来,我进去以后到那了一拦,问怎么回事,我说来开会,然后就看工作证,然后打电话,确实那边一确认——也没有监控探头——就进去了,知道摸索着前进,对吧?然后当他也很快迎出来了就过去了,然后把自行车找地方一停,带着我参观紫光阁,参观他们的食堂诸如此类的,对吧?我们去中南海,他就这么就进去了。
在这里头你一定要明白,很多的时候,它不是你想的那种情况,因为我们就是说的你注意力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基本上出错概率非常小,对吧?但是他因为是人,他就会出疏漏,就会有bug,没有办法。所以说从质量管理上,我原来学过质量管理嘛,就是说从质量管理上来说,只要是人生产的东西它一定会有问题,因为人就是不完美的,他没法完美。对吧?它必然的就会出问题,我们做的就是减少出错误的那种可能性而已。所以包括这回长征三发卫星,15亿就报销了……然后紧接着发的文章,我们其实发卫星特别多,那意思这都是小问题,反正淡化这个东西。真的,其实你一定要理解他没有什么,大家都是凡人,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它会放大你。
因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原来在轻工业系统工作的时候,因为这东西都是盘子碗,他觉得你陶瓷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一旦用在一个关键的场合,比如火箭上卫星上,你这上火箭了!其实有时难度还不如造盘子,为什么很简单,大家稍微学了化学以后就能明白,你造这个玩意儿,它是天然矿物,我做那个东西都可以用化学纯的,甚至用分析纯的都可以,所以那个东西是可控的更高,它只是那个场景,让你觉得长征火箭上还有你做的东西,就怎么样?这碗是你做的他没有感觉,从来没有。但是其实从技术难度上未必就比他容易,但是我们觉得那个东西特别稀有,所以我们觉得不一样。所以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搞这个就是火箭发射,因为参加过航天工程的一些边缘的前沿研究的时候,就出现过这种问题,就是讲航天的成本为什么那么高? 他要排除各种的不确定,对吧?你比如说标准件买螺丝他不敢买,他不敢到街上去买,因为你不知道他怎么弄,它很便宜——你发觉(问题)了吧——但是万一出了事咋办?只能自己做,因为我们是可控的事,我们可追溯的或者材料,钢材或者什么加工件都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追溯的、可以控制、可以检验的。所以这么贵,你是做出来,螺丝做完了可能跟金子差不多了,因为批量太小嘛,他也不能到街上买。就是他的这种要求把自己锁死在这。
包括比如人不喜欢被控制,都是我们讲很多东西的发展一定是不可控的,就包括我去(重庆),我也没想,比如说我要学家哲学,我去了以后,我在那个瞬间、在那个过程,我在不断的试错纠错,出错误再纠正。所以印象最深的就是去了以后,当然廖老师过去她老压榨我,但是我要保护自己对吧?就这4天,我说一定有一天我得自由,我说这7天还歇两天,她要4天全给你派活,但是她老弄一些小阴谋,我们中午一起吃饭之类,我心想你那饭我能白吃,我不吃。她说有人管饭,我说我也不吃,反正就不见面,那一天不见面,她说你去哪?我说我看博物馆,然后就跟刚才我说的重庆通,我就讲我要看博物馆,他说你看什么博物馆?我说我就来了重庆看了不少的博物馆,抗战博物馆——就是当时蒋介石和美军参谋顾问团住的南山上头,宋美龄同学什么都住在那,那上头我已经去了两次了,我说别的也不看了,我说我就想看看重庆博物馆。但是问像90后的小朋友,我说有什么重庆有什么博物馆?回答说三峡博物馆,然后后来我就跟这个人说,我说我想看的就是重庆对吧?因为来那么多次重庆,要看看重庆的历史的发展的沿革和这些东西我比较有兴趣。因为很多东西可能在这儿不在这看,你可能就看不到了。
他说行。第二天来车接我了,咱们怎么走?他说跟那司机说走去三峡博物馆,我说不去,他说你不知道三峡博物馆和重庆博物馆是两块牌子一个地方了。你知道三峡显得很大,你知道吧?大家都认为喜欢看三峡,你知道吗?结果到那以后,他那个东西所有的东西,各种logo,包括什么纪念封上都是重庆博物馆。然后我去那看,刚才我们也讨论过抽象和具体的问题,对吧?我们就具体了,因为到重庆博物馆了,然后镇馆之宝是一个在成都挖出来的一个汉代石刻像。我说怎么回事对吧?他说你看你忘了吧?dang中央在这设过西南局,就刚解放的时候,你像邓小平,包括贺龙、刘伯承都在重庆。那阵挖出来的东西,川渝挖出来的东西都送到领导在的那个地方去,知道吧?这就是重庆的文物里头有大量成都的。
所以在这个里头我们其实包括你看跟学生交流的时候也出现这个问题,就什么就是说我们容易给概念,但是概念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涵括性好,但他有一个问题就什么没法操作,你看这个孩子经常会说老师我的数学不好,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概念。对吧?我多次强调就是数学,不是两个字,是你三角几何不好,对吧?还是解析几何不好,对吧?还是其他的什么代数部分不好,对不对?不然的话,这个就没法解决,我身体不好,什么叫身体不好,这等于跟没说差不多,对吧?你特别进了医院以后,他得先定位。但是这种空的东西你可以看,一下好像都在里头,但是其实没法落地、没法操作、没法解决。所以在这个里头我就跟很多的学生就说,我说你都高三了,你不可能数学一路都不及格,还能上到高三,对不对?肯定你是数学哪些部分不行。
但是我们容易做什么呢,因为我们受到伤害以后,我们想提高对自己的保卫,我这时候我才破解了,除了潜意识,比如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它还是什么?它是一个概念,概念就是蛇状物的威胁,它是一个抽象,不是一个活的蛇,对吧?因为我被蛇咬了,你拿一个塑料蛇,你看我已经开始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各种恐惧来了,为什么?我是一个对概念的恐惧,对不对?我不是一个真实的蛇的恐惧,因为我恐惧了怎么办?我就形成了一个恐惧的概念,概念就把防御区域扩大了,引来的副产品是什么?安全区、舒适区形成了。对吧?他拿个草绳子,我这已经快崩溃了,你看见没有?因为我的那个东西太小了。所以在这个里头我们其实所有的解决问题,你如果不落实,就像你说的大家好像都明白,就都不明白。因为你的数学里头的东西就不一样。数学你知道大家是在说数学没说英语,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不落实到比如说是三角函数还是解析几何,对吧?还是二次函数或者什么一元二次方程,什么诸如此类的,你不落到节点上,你处理、解决问题就都不行。
所以你可以看要有概念,但是一定要具体,你不要不具体。其实很多的问题就永远是含糊的,就是大家好像都在说数学,或者大家都在说博物馆,你看没有到最后你才能落实到一个东西,然后我们才能通过一个个东西再提炼出来。不然的话他都是空的,对吧?我们常说要抓紧,其实就跟没说差不了太多。对吧?然后你把deadline给出来,内容给出来,你才可控,对吧?你的进度才能保证,不然的话就然后你说强调多少次,要抓紧,你看见了吧,然后就没办法。但是你可以发觉这里头说回来就是领袖很困难,领袖只能讲孔子。领袖只能讲大词。但是一旦大词它一定是概念,绝对不是一个细节,他没法弄。所以这个里头他的影响力,包括我说的,你比如它的管控,他实现不了,就在这:人的本能就是不喜欢被控制。
“我们是中华民族”,有人就直接问了说钓鱼台收不收回来,跟你卖煎饼有关系吗?今天你煎饼卖不出去更重要,钓鱼台没收回来,你就不准备卖煎饼,你准备去钓鱼台了,对不对?因为大家其实要生活,而且在这里头杨先生还讲了一个,我也讲了,觉得讲得挺好,关于“life”(可译为生活或者活着)。在洋人那,生活和活着是分不清的,中国人是不一样的,你看到没有?因为如果在这个词的那种考究越多,他显然就是关注的强度不一样。这个是可以证明的,对吧?他用更多的词,包括亲戚的关系对吧?那么就是从哪边论是怎么样?从你妈那边论,从父亲那论,你看说对吧?他肯定是对这个家族的东西重视,他才去琢磨。外国人排第3名才有亲爹。所以在这个里头,我自己觉得用一种开放的更认真的态度,开放的同时还要认真这个东西,很多人讲怎么弄,那就得足够多,就像你对吧?你那个车技要好,你就得开足够的公里数,也没有什么knowhow。
潘潘:我觉得我看完这问题,我能想到我对我自愈的理解。在周围家长的推广,其实遇到了挺大问题,因为自愈本身就是一个挺抽象的概念,然后我之所以想推广,是……
李林溪:是“自我痊愈”那几个字?对这个我还得细问一下。
潘潘:对,自我痊愈主要就是针对感冒、发烧、咳嗽、流鼻涕这个事情就不要吃药,尤其是针对小孩子,就大人你折腾罢了,我是觉得小孩子那么天然健康的一个身体,然后因为大人自身的无知,然后给孩子盲目地用药,就导致孩子身体越来越差劲。我觉得这样不好,而且是我自己本身从小的生长环境就是被过度用药,因为我爸是军人,然后军属看病是不要钱,而且我们家那边离医院也不远,然后我妈妈本来可能我生下来又过胖,就免疫力不好。小时候上小学之前差不多就一两个星期就要住一次院,动不动就什么扁桃体又发炎、气管炎,就各种炎,然后还得过那种百日咳,就快半年都没有好的那种咳嗽,然后还打过一个月的那种点滴,最后打到人家都说觉得快要白血病了,白细胞已经到很夸张的地步了。
但是我现在看来,我觉得我完全过度医疗的牺牲品,差一点就身体被摧毁了。所以我就比较在意孩子的这些健康问题,然后幸运地了解到这个东西。开始我也是很质疑的,就开始也没有过多的关注,但是后来因为真的孩子经历发烧了,我就开始咬牙去尝试:发烧了,我不给他用退烧药。我认同发烧这个事情,它是身体的一个免疫反应过程。因为你身体是通过提高温度提来消灭这些病毒,因为确实我也没有那么勤快地研究医学理论,但是我通俗地就通过传播者一些通俗的讲解,我是比较认同的。我也觉得因为你想想孩子发烧是烧不坏的,但是用药你觉得可能是你看不到,但是它对身体也行的伤害,其实你是看不到你也无法估量的。对你这与其多发几次烧,那是比起多吃几次药,我愿意多发几次烧我觉得没关系。反而很多家长觉得烧出肺炎,我还不如吃点药给他压住,有这种理解。但是我通过这几次,反正现在我在面对我们家孩子发烧咳嗽,我是非常淡定的。
梁先生:就变得从容。
潘潘:我就不会用量体温,就哪怕它烧成火炉,她跟我说难受,我都告诉她,我说我给她讲道理,她好像也能接受,虽然哭也闹,但我可以抱她一整晚,她现在基本发烧就最多两晚,平常就是一年发烧个三、四次。然后只要发烧一晚上就第二天又活蹦乱跳了,其他什么都不耽误。但大多数其他的孩子都是一烧就慌,然后就退烧,说怎么也推不下去,然后吃了几天退烧药之后就说转肺炎了,又去医院打点滴,就身边好多这样的。然后我也知道这个东西,你要过多地说,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肯定是入邪教了,你想怎么样?对,会有防御。
所以我会相对很简单的先给人说一句,如果人家感兴趣我再尝试着多说,但是目前看下来,我觉得是90%的家长是不相信我的,他会相信用药,他会相信医生,他会相信大多数家长所做的就退烧药一定会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无奈,但是我觉得我也只尽力就好吧,我也不能强求。
山子:一定要注意人有个体差异,可能你们姑娘是可以挺过去的,但是有些人的孩子挺不过去。
潘潘:我也认同,这个一定是家长自己的来判断。
全贞雪:有时候是能挺过去,看人。
山子:或者说你们姑娘比你小时候自己壮一点。
潘潘:对,那也是。
李林溪:我在想另外一个,就是我在讲课的时候想到的,有些在没有共情的基础上不要轻易打比方,就不要他们在没有这个共同体认同,它是不认同的。用比喻这个东西去说明一个事情,还是在有认同基础上才去做。
梁先生: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就陷入一种我执,即我都是对的,我又没害你,我为你好,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他都会自己往外蹦,那么一旦蹦出来以后,特别是你自己有那种临场的感觉,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太好了,我应该让大家更多的知道更多的去接纳什么,这些东西就出现了。这个一定要审慎,特别的关键。
山子:林溪提的这个问题,我自己感觉中医内部这个问题特别大,就是基础概念不一样,你说的气血跟我说的气血可能完全两码事。
李林溪:而且大家觉得好像是一码事。
山子:完全是各自为政。然后这个东西我这段时间在想,我跟先生也提了一点,我自己想写一点这样的东西,比如西医它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有全世界统一的标准,还有那种非常直接明显患者都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然后他就可以大量的复制,而且大量迅速简单地复制,而且大家都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而且操作起来也就比较标准,比较靠谱。我一直在想内经伤寒的为什么没有这些东西?既然他这么好,既然老祖宗那么聪明,为什么他不能弄这些东西?
李林溪:我另外想的就是人的本性就是对一个全面的东西其实是排斥的,就是理性(运用)需要花精力,人就是比较懒的,用感性理解大多数东西。对全面客观往往不太——觉得我需要花精力——他可能不太接受。对片面和极端的他可能他更认同,这才是符合本性的东西。那个是反本能。
梁先生:其实不用绕,你一看就讲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对吧?你用大脑1思考还是用大脑2思考就在这,对吧?它是快速的。所以包括我讲过的余英时,他讲你五四运动普及了科学概念,但是没有真正让中国人弄明白科学理念,你知道吗?所谓科学概念,“因为”、“所以”他整明白了,你知道吧?而且没有我就不行,就简单直接。你可以看传销,我原来是什么样?现在我已经多少钱了,包括可能是保定那边的也是一个传销,然后车牌还是都是什么,反正都一样,都是买成一样的,然后这个是中央支持的,一听,对吧?你想这种事他中央支持肯定就是骗子。
包括子钰的项目,后来我去问了怎么回事?后来看样子是事就是经济上能不能盈利不太清楚,但是诈骗的可能性接近于0。你知道吧?原来就是我父亲不是住在北大承泽园那吗?承泽园北边,那边是旧的园区,有山、有水、有桥、有亭子,但是现在都拆了,全都给弄没了。那部分平房当时都是给北大里的工人的宿舍区,他们肯定也不住,因为很值钱,租出去以后,当时有一个公益组织——一耽学堂,他们在那干。所以我认得子钰是子钰先认得我父亲我才认得子钰,因为一耽学堂就让她负责跟我父亲联系,你知道吗?就一回二回,老见着她就打招呼,然后她就说她在中医药大学读硕士,然后她主动介绍她的导师,她一叫导师,我就明白了,她的导师不是曲黎敏吗,曲黎敏我认得!这样你知道吧?后来这样子钰通过这条关系来读书会、来心理讲座的。然后她现在弄这个项目的人,据说是十多年在一耽学堂当义工的两口子,一直当义工,现在就跑到山东菏泽去搞一个类似于绿色种植这么一个项目。然后他负责人跟我又在一个微信群里头我就问了一下,因为各种借钱,我就担心。我就问一耽学堂负责人逄飞,然后怎么样,好,这一问又出别的故事了,“梁老师,你来参加吧!梁先生写乡村建设这么有名,你来了他等于给他们站台了”。我知道子钰没掉坑里就行了,我就不下水了。
全贞雪:那种抽象概念阐述,我是给这个学期我给学西医的人讲中医嘛。你要想讲给他们讲阴阳五行,按中医的内容来说,什么山背面是阴,让人家跟真的根本听不进去,你还得是他们原来的固有思维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也按他们的路子上进去。所以给他们讲阴阳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拿生物来说,因为生物的状态它是跟生命相关的,生命的能量循环相关的,生命的遗传物质的传递也是他也有基因里面也有迟钝的基因和有一些比较敏感的基因。敏感的基因,它就是可以快速的做反应;迟钝的基因,它就是先不快速,他要听外面的各种汇报之后,它才会发挥这种的,所以这里面就有那迟钝,就偏阴;偏敏感的就偏阳。生命状态就是相通的,所以用这些来跟他们讲的话,他们会觉得能中医不玄,然后中医确实跟生活、人、生命状态有关系,所以他就会比较愿意去听,或者是愿意去跟你聊这些他自身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抽象的概念要跟人家说的话,最好还是把抽象里面真的这剥离出来,变成一个他们所听懂的,哪怕是一部分。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都说的进去,但是举个这里面的这种一两个这样的例子,他们慢慢就接受这个概念,然后可以用这个概念来可以想。所以觉得以前我就觉得我们老师说的杂学,我有时候也不是说真的去各种的听。就讲课的时候,我可能想起我就会备课之前会想到可以说说内容,就可以还觉得还比较好用,所以课堂效果也感觉上我自己也比较满意,他们也还反馈这些方面上也还会好一些。
然后不同的人定义含糊不同,我觉得对生活的定义含糊不清的时候特别多。然后我们科里就没几个人,就8个人,这还是针灸、理疗、中医放在一块的这么一个科里面,就分奖金这个事儿就能把人给闹腾死了。作为领导来说,应该是你的方案是差不多定了之后大家有各种出入嘛,因为有些有奖励奖惩这种的。可是有些人作为一个自己就是一个平民,就平头百姓还非得要对着领导说,我要看我的这个是怎么形成的,你给我报告一下我的工作量是什么样的,别人的工作量是什么样的。我想想这个事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你算老几,领导是什么?给你报告的,什么传话筒还给你计算完了报告给你。
怎么能有对事情的理解(差异巨大),而就完全那么去办事的人,我就觉得颠覆了我的世界观。
潘潘:我没太理解,是说他想他希望奖金分配方案是完全公开透明,他想了解每一个人的计算方式对不对?(对的)不可能在体系里边大家都一样的。
全贞雪:而且他就是说我不仅知道,我要看看他的为什么是这样,他就没有这隐私的概念,他说我就得要公开的,我要知道,就说我要知道奖金怎么分出来。奖金,如果管理层没有模糊地带,他还管理什么,它就是给你计算的了。
潘潘:企业最忌讳说彼此知道工资,如果这样包括企业就会严肃处理。
全贞雪:对这个事情对他来说,他觉得他不能接受(要搞清楚)。所以我们单位也比较有那些糊涂的人,因为他这么麻烦,就老是去找人力、财务,老去磨,慢慢他也磨出来,财务被他磨得真的给他数据,我就觉得也太没有原则。我就觉得太可怕,不是我们不能理解的状态。而且我们领导确实刚上去的嘛,跟我们同岁,所以他也觉得我能给你知道,你愿意看去看,我是一点都没有私心的。但是他要是往私心方面上说,我觉得对他的目的是要把这部分澄清,我觉得领导者应该是针对他这种行为,指出这是越界,一开始就把这个行为给压下来才可以,结果转变状态有点不太一样。就各种各种人的理解方式,我觉得为人处事的理解方式,原来人和人之间有这么大的差异,我觉得就差个1000块钱,结果找来找去发现是人家还给多发了。就这样1000块钱你损失了,你有必要把整个科里的人都得罪翻了,然后就这么做事吗?就觉得没法理解这种生活方式,反正也能看出来他活得不开心,可是怎么就惯出这样的毛病来了,我也懒得理解这种人,咱们不是说不一样的人,你前面就不一样的人,是不是要分开,我情感上我就是想跟他离的远一点,跟这种人还是不是一个路子,就别在一块不,但这是多样性吗?
李林溪:更趋向于概念上的,比如西红柿炒鸡蛋,放糖的,跟放盐的,原来都坐一块吃,现在非得一定是自己边的,不能认同彼此的存在。
全贞雪:看来我们也认同有这样人的存在。
梁先生:而且你得理解我记得跟大家讲过,蟑螂一定比熊猫多,对吧?而且蟑螂一定比熊猫顽强,这种是完全没有办法,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对吧?所以不用抢救蟑螂只有抢救熊猫,所以在这里头包括我自己也多次提过,我们一定要明白社会是圣人社会还是凡人社会,对吧?如果你认定是一个圣人社会,就很麻烦,大家都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自我要求的标准,然后你会很郁闷,觉得怎么还有这样的人,还有那样的人,对吧?所以一定是各种奇葩的人,他都有,而且才会健康地生活。
所谓的健康就是按照他的模式去过他的生活,而且这个时候很多东西对我们自己来说要破一个东西,就是破僵固型思维:就是应该、必须这样、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直接的杠杆。返回来,包括像潘潘讲的那些很多东西他不接受是一个概率的世界,要求一个绝对可控,对吧?因为你病你让他的那种所谓的抵抗力去说……你不能拿秤称,也不能拿尺子量,然后你说这等会就出来了,我看着慌。
潘潘:温度是会看到直接的数字,下来以后,很心安。
梁先生:但是问题在那第一次去冲击的时候,他是慌的,所以很多东西,在这里头你可以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能不能把它具体化,对吧?就是一看数学脑袋大了,这不是你看他考什么数学,对不对?然后你才能应对的办法,只要你不准备罢考,你还得进考场,对不对?你就要明白他考什么数学,而不是考数学,我要死了,然后完了,对吗?它得解决具体的问题。
这样的情况下,你发现没有这个越清晰,其实恐惧就越小;越朦胧,恐惧就越大,因为它没有边界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头,它是基本的这种底层的概念的建立不行,然后他就不断的出问题。所以我去讲,这回包括我们这块一直讲家庭教育或者家哲学、家文化讲了半天的时候,因为一开始也是党关心民生、民众福利什么之类的,所以第一次课是在区党校里头讲的。区党校,而且算是党的关心群众的一部分嘛,所以这样情况下,对党校的常务副校长也参加了。最后第二天我们开研讨会,他还跑去了,我们是在山上,在村里头他还去了。然后就研讨会,他大概觉得他是领导要讲两句,大家在那讲的挺热闹,他突然讲:你们讲的都对,但是我觉得家庭教育一定要注意,一定要以国家为重,要舍小家保大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样我们的家庭教育才能讲到点子上。他这个本行他一定会讲这些东西出来。对吧?所以大家都就笑。
全贞雪:他还觉得无比正确是吗?
梁先生:然后美国来的那个人就恼火,他说我问几个问题,大家讨论,就说这问题是先有家还是先有国?家和国哪个排第一位,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听明白了嘛。我说我在微信上——我没有就让他打消,就坐我旁边——我在微信上看过,有人讲说没有国哪有家,然后人家底下往上跟,没有饭,哪有米,没有墙哪有砖,对。没有河哪有水……对吧?不能直接撅他,但是大家一听都明白,对吧?你不是说他方向不对,他一弄就成了一个政治的东西,他不是去针对我们讨论当下的问题和我们自己要真正去解决的。就跑偏了以后就给跑成德行。
全贞雪:在职场,我就发现原来像我们这样想的,一直我觉得我周围都是像我们这样想的人,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像我们这样想的人真的是少部分。
梁先生:因为思维,他犯懒,这是一个惰性,他也是节约能源什么之类的,他就不愿意深入,他就愿意在一个浅表,所以他很快就说药下去以后几天能退烧;药下去了,几天就能上班,他都是这样的要求,对吧?他根本不管其它,因为他看不到,他不愿意往深了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你也得理解他,大多数人是这样。所以返回来正因为你少,所以你可以看潘潘,她去让闺女这种一旦一次一次成功地去这样的话,其实她也好,闺女也好,其实心态就变得不一样。而且她对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是那种斯金纳操作条件反射似的东西,那么焦虑。
全贞雪:你(潘潘)只要有一个点,非得去医院的点,你掌握的准确了就可以,孩子的呼吸是喘的、憋的那是要去的。
潘潘:明白,对这个事还真是……像我不感冒一个星期了吗?之前我咳嗽什么,但是我自己感觉我是病毒性的,我是可以的,OK的,然后又高烧有低烧,慢慢的现在基本痊愈了。然后我妈妈让我很生气的一点就是昨天她跟我说,大前天的晚上她就喘不上来气了,躺着就快窒息了,然后坐着睡一晚。她过了两天才告诉我,然后我就很着急,因为我们觉得影响呼吸,看过很多案例,这种急性病毒容易转肺炎,什么衰竭的,然后要领她看病,非说自己没事,反正这两天可就乱吃药,我怎么跟她讲也讲不通,别说别人,我自己身边人我都说服不了。
我老公也说,我觉得自己明白是下呼吸道还是上呼吸道,然后对头就吃什么药,反正也都能好,然后反正我们基本上各自为政这样的,不是,然后谁也不管谁,但是我们家孩子是我说了算。其他人跟我闹翻,包括婆婆翻脸什么的,说虐待孩子怎么着的,我说我孩子我负责,我能管住我和我孩子,然后其他人各自管各自就是这种状态。但是确实我妈影响呼吸了,但是不管是什么药她自己熬过来了,我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就影响呼吸会很严重。
全贞雪:主要有这个点掌握了,其实烧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烧带来到后面的整个衰竭、系统衰竭是可怕的。
李林溪:好吧,今天就先到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