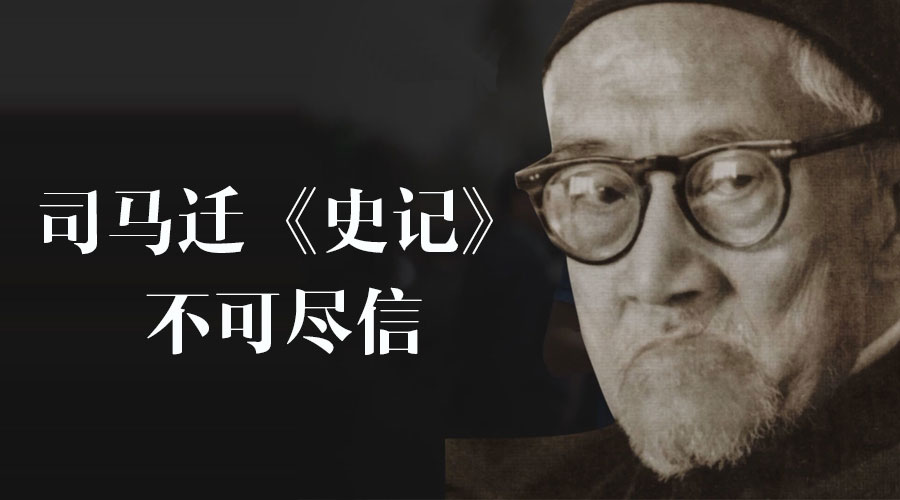昔人不尝有“信史”之称乎?而司马迁《史记》乃多不可信。近者我撰写《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就《史记》以考孔子事迹,乃嗟讶于其荒谬有失史职。
司马迁上距孔子之时不过四五百年,虽非甚近,亦不算甚远,苟能忠于史职,则于孔子生平事迹尽力考求,应当可以就周秦间子史诸书所流传者有所订正,汰去芜乱伪误之说,或审慎存疑,不轻予记录。然而马迁竟未能也。其所为《孔子世家》滥取诸书,不加别择,似只求博闻,未计其他,以致其书内(非单指《世家》一篇之内)自相抵触谬戾者不一而足。自己且不求信,其何以取信于人?
考求孔子言论行事自必首先求之《论语》,史迁所为《孔子世家》一篇大体依据《论语》,不为不是。然《论语》一书既有不同之传本,便见得其不尽可依据,而宜掌握其他书史互相勘对考校,以求一是。《论语》多有显属错误之记事,例如《季氏篇》首章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一事,按之史实子路为季氏宰在鲁定公世,冉有为季氏宰则在哀公世,并非同时,何得有如《论语》上那许多问答的话。又如所记公山不狃召孔子事及佛肸召孔子事,按之《春秋》、《经》、《传》及其他书史均错谬可笑。然而史迁竟不加核订,以讹传讹。如此之例尚多,不备举。最可怪者《史记》依孔子年龄早暮以次著其事迹,仿佛很认真,而其实乃错乱不堪。
《论语》不尽足据,其稍后于孔子之诸子百家言,更不足据。吾文对于史迁的许多错误不及指摘,最好请参看崔东壁《洙泗考信录》。此书是为孔子一生言行清除伪误传说的一部好书。其核求真实像一个科学家,但因其力避世俗浅陋之见,有时立论又难免主观。虽有难免主观之嫌,我却多半赞同之。——作者此因孔子名声广大,非独传阅辗转多有错讹,而被人虚造借喻之宣言尤多至不可胜数;《史记》于此每不加甄别,杂收滥取。其不负责任乎?抑识见不足欤!
如下两例可见其无识之一斑: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
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孔子当时声誉虽高,未必广泛地被称为圣人。且人之所以为圣人,亦岂在乎其博闻强记,善能解答一些奇闻怪事。似此根本不值得载入史册之鄙陋传说而竟以入史,则迁之识见不高是肯定的了。对于吾国伟大史家说他缺乏识见,在我是于心不忍的,其奈事实之不可掩何!
末后我要指出史迁思想上之偏蔽。他是对儒家抱有偏见的一个人。《孔子世家》文内叙及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记有老子的一段话;又在《老子韩非列传》内记有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回答的一段话。两段话词句不同,而词旨在肆其讥诮则同。兹照录其后一段话以及孔子赞叹老子的话于左:原稿系竖写,从右至左排列。——编者。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夫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孔子问礼于老子,大概曾有其事,今见于《礼记?曾子问》篇内。篇内所记与史迁所记不同,自可置之不谈,但在《史记》一书之内,同记此一事而竟然记出来前后不同的两段话,此岂忠实记事者之所为乎?两段说话不同,而词旨讥诮则又同,那明明是文章撰作者的把戏了!结尾是孔子赞叹老子犹龙,一抑一扬,史迁之意昭然若揭。
史迁所以如此者,是有其由来的。试检《太史公自序》,一读迁父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旨”便不难明白。原文不长而于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各有论断。在论断中总是一分为二,有所肯定,有所否定。对于儒家虽亦有其肯定之一面,却一上来就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从……”
对于道家却称赞为融合了所有各家之长的,如原文: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原文临末又就“形”“神”二字,发挥道家学旨,说: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这不是明白地崇道家而贬儒家吗?司马迁正是一秉其老父的思想而写书;我说他思想上有所偏蔽,即指此。他在《老子韩非列传》中便点出了两学派的矛盾斗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
“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然则《史记》之为书,尊老子,抑孔子,史迁固不自隐讳。
附言:儒家之学,道家之学,同传自远古,皆是早熟的中国文化产物,各有其不可磨灭的学术价值,方将在人类未来文化中得到讲求,我在《东方学术概论》一书中略有阐明,可参看。
补记:
适从崔著《补上古考信录》中得见其转录宋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一文,有如下的两句话:
(上略)至有博学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于是尽集诸说而论次,初无所择而唯恐遗之也,如司马迁《史记》是已。
此其评断史迁与我的话不若合符节乎?其言早在千年之前,惜我乃未之知也。欧阳尝撰有《新五代史》传于世,固属一史学者。
1974年10月30日属草
附录:
《史记》一书为吾国文化历史一重要典籍,必须读之,但史公为此亦殊有缺点:(一)叙述史实往往重趣味,似小说故事,虽文章引人入胜,非史家正体。恐其于当时社会政治实况缺略不周。(二)老子道家一派之学为其父所最推重,竟于老子之人未能深考,迷离惝恍其辞。如其汉初尚不深考,后人去古愈远,更无法考知了。(三)儒墨为古时两大学派,竟不为墨子列传,只附见一笔于旁处,缺憾甚大。
(摘自《致田慕周》,19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