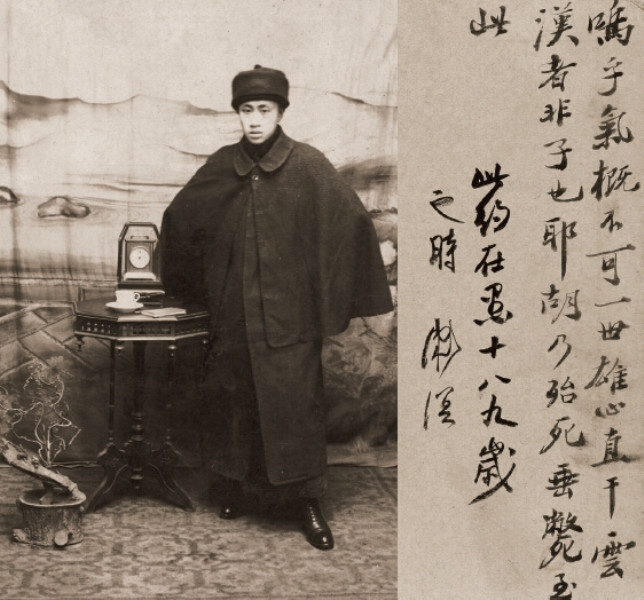第127次读书会《朝话·我的自学小史·八、中学时期之自学》整理稿
主讲:李纪川 督导:全贞雪
李:
“真的自学,是由于向上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人生问题,二社会问题……”
“凡事看他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调转来……恰与西洋这些功利派思想相近。”
- 请结合自身感悟,你是否认同梁老以上所做出的概括;或者从哪(几)件亲身经历的事件后,你也得到了相似的体悟;目前我们自己所追求的问题是哪些?或者想不断向上的领域是哪些方面?
我先说一下出这道题的原因,之所以想到讨论自学这个点,与我这半年来在新西兰的一些见闻有关,我感觉到两国的教育在理念上存在差异,我曾有几次去我的老板家做客,我老板的女儿今年上高中毕业班,给我的触动是,和中国高中生思想上的差异,有时感到她的思想有一些单纯,但是在能动性上非常突出。这段时间和包括我老板在内的一些当地华人交流得知,这边的文化课教育可能没有国内的深度,但孩子们很早就能学会烹饪,会排练戏剧,演出话剧,很早能学会在野外露营如何使用专业工具,能够自己弄出篝火,搭帐篷。
回忆自己小时候,其实我对以上这些事务是挺有兴趣的,苦于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国内现在恐怕多数孩子也还是相似的状况吧,或者成本很高。我感觉他们(新西兰)的教育更在意的是教导小孩如何在毕业进入社会时候能很快融入,很快适应这个社会,换言之,当到了一个相对陌生的地方,能够凭自己所学很快融入,而不是对学了多少文化知识做高要求,我认为这是建立自信心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可以说我是羡慕能在青春期就接触并了解这种世界的丰富的孩子们的。以上是我对看到的现象给出的解释。
回到题目,由于我在国内长大,从来只受到国内文化教育的影响,看到不同的东西后有些疑惑,自己的小孩应该如何培养?
全:
他们的英文课主要是什么样的?
李:
我了解到的有留下阅读作业,然后自己去社区图书馆找书找资料,大家课上进行讨论并完成的。那边的小孩好像很喜欢自学,阅读。我了解到的信息很多小孩完全出于自发去读书。
冯: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国内可能为了模仿国外培养孩子自己研究,不要总是被老师灌输知识,抛出问题自己去搞研究,我们名校的某些小学生们,创造出了很牛的论文,惊艳了朋友圈,大家看后感觉说这种水平的论文,简直是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水平。比如对古诗词,陶渊明等人的作品做大数据分析啊,研究作品里某些词或字出现的频次,发现作者的喜好啊等;后来再深挖,发现这些中关村X小的孩子们的父母本身就是搞科研的,博士,教授的水平。结果可能是老师提了一个高要求的作业,家长们不甘示弱,纷纷冲锋陷阵,交出一份份看似很完美的作品,学校一顿表彰,等到了互联网里大家一读,就产生了质疑,刚开始大家都觉得很惊艳,但更多人产生疑问,这会是一个上小学的小孩子的水平吗?做出这种文章的小学生他自己参与了多少?他能收获的又有多少?还只是说为了一个结果而去做?可能国外课上老师给问题让自己去解决,这种教育不在乎结果,在乎的是整个过程,国内呢主题永远是竞争,所以只要结果,不理会过程。
梁:
我个人倒不是反对竞争,但是他现在造成一个混乱的现状,大家看到都是一个一个的动作,比如某人考了多少分,去了清华或者北大,然后我们都按照那个动作去弄,(这么学的结果是)他可能张不开嘴,不会说,但是可以把雅思成绩给考到极限,我们是这么玩儿的,所以能把外国人给考晕了,但是真的去实用,就不灵了。这是因为它是人造的,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弄出什么来,你要这个指标,我就用各种办法把这个指标给你推上去,然后完事,所以在这里我想说的更深层次上得有一个醒察才行,不从深层次去看,仅仅做讨论,我觉得讨论不动,他(梁老)讲过一个问题,就是五四运动对现代中国发展的伤害。我们老觉得它(运动)帮助我们了,肯定是有帮助,但是也有很大的伤害,这个伤害在哪儿,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搞起来的口号,首先,把传统文化彻底推翻,打倒孔家店,那个(传统文化)彻底不行,我们要换新的,对吧;这个手推车不行,我们要换火车,所以咣一下子把手推车扔旮旯里去了。问题在于结果是,马上大家去学知识,他认为是通过知识去解决问题,因为原来搞科举的时候,不管是八股文还是什么也好,你还得自己去琢磨,没有统一,八股文它即使那么“八股”,它没有标准答案,但现在机读卡考试可以搞成这样的;结果这么一弄,(学术)反而给弄得更僵死,比八股还死。洋人都不敢这么弄,我们却敢:你要指标我就弄指标,你要分量我就去添分量,直接这么玩儿。洋人觉得这样不行,不管是出于神造世界的信仰也好,出于对上帝的谦恭也好,他们不敢这么弄;我们不管,我们直接招呼,我们直接去凑数据去。这样一弄,人就变得更不像人了。
我的感触特别深,在于我一直从事临床心理咨询,我见到(病号)学生他们一直被“拧”到这种程度,他受不了,崩溃了,都是这种问题。很多(中国)学生是按着“导航仪”的指示去把高考拿下来的,听话,跟着干……好使,然后可以去到211,985。完了到那儿以后,瞎菜了,没有导航了,或者导航不好使了;因为得自由操作了,特别是(大学里)更抽象的那些东西不可能像高考那样模板化,虽然有教学大纲,但各个学校的高数其实还是不一样的,还是有侧重的。专业课里也有这种情况,怎么办?它不可能再弄成高考一样的形式了,一堆规定动作。所以中国弄得最精彩的是什么,就是阅兵式,(间距)多少厘米多少厘米,手抬多高,弄那么精确,就这么弄。要是外国人肯定都疯掉了,这太无聊了,但我们看着很HIGH,这是自我价值感虚弱的时候,我们凑成一体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强大,他是通过这个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的。但是你想象那个过程,抛开政治什么的因素,你盯着它(阅兵式)看,你也得崩溃,太无聊了。我曾经见过一位流落街头的前国旗班的,他就会干这个,其他什么都不会,(生活)没办法,成了一个机器人了。在这里我们要注意,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人生去怎么安排,我们要挣钱,要轻松,要去旅游,要多少万……你看,人,生活没有了,全都是一块一块的指标样的东西,让你自己去过这样的日子是要崩溃的,真的是过不下去。因为这个状况下你不能有自觉,所有动作都得按照指令去做。我爷爷(梁老)说过,一个人失去了自觉,就会感觉自己像一个东西,而不像一个人。因为你完全不能自控了,就是按照规定,抬手,抬脚,左转,右转,完了,就可以到(目标),你有成就感吗?没有。你只会有侥幸感:没掉队。你绝对不会兴奋,比如你自己找一个地方,找来找去,最后到了,你会有成就感;那你跟着导航仪,你到了,完了。
问题在于人活着一定要活一个生活的趣味,生活没有趣味了,你肯定要疯掉,一会儿就不行了,就跟卓别林《摩登时代》里拧螺丝似的,拧着拧着就拧不动了,虽然你拧一下多少钱,是能算出来的。有很多时候你的表达是解决不了的,比如在心理所学习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畅想,你最喜欢做什么,我说:喜欢当农民,因为农民最大的特点是和大自然有交互的,那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因为我们有那种长时间的匮乏。我今年看到祖父的日记,他们被政协组织1961年到厦门,跟郁美中先生去买东西,买不到,没票。日记记录:购物不得。没有凭证,这种长时间的匮乏的刺激,造成了这一代人的感觉的偏执,就是他们对物质的东西的强调,你可以看到,特别是东北人受到影响特别深,工作千方百计要进到体制内,就是为了安全,安全压倒一切,你甭管挣多挣少,那年招厕所保洁员,硕士生都去报名了,因为可以给事业编制,就这么玩儿。这种非理性的行为,一定不是思想的问题,而是潜意识的问题。因为(这些行为)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他内心存在深深的恐惧。我在咨询当中看到社会不断的出问题,已经看到00后开始出问题。这个就会不断的产生问题让我去自学,比如最近又有一波抑郁症上来了,所以(我)赶紧找到以前做的抑郁症的案例和资料,又拿来复习。
那天在微信上和山子有交流,我说了一个事情,其实有一个行为特别好解释,就是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现在不在乎当下,就告诉你忍着啊,忍着忍着你就去北青了,北青就可以怎么样,金领就可以怎么样,就这么弄,然后给你一个一个台阶弄好了。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不能活在当下?没有安全感,你没有勇气面对当下,就是你不敢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去寻找生活的乐趣。你现在就是高中生,就得苦逼,就得刷题,不刷题你就死了。所有案例都是这样,用慢慢的恐惧去驱动自己的个体行为。所有孩子都苦逼,但是大家都苦逼了以后就无所谓,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快乐的。本来可以不这样,但他(社会?)非要把他拧成这样,而且把这个东西搞成了主旋律,这是最大的矛盾。不是你想不想放松的问题,而是你没法放松,大家都是焦虑的,老师比你焦虑的厉害。
现在有好多地方请我去弄个什么(青少年心理辅导)中心,听完了以后我跟他(赞助商)讲,我想从学龄前开始弄,但他们要求先出尖子,弄北青,他就要立竿见影。我当然也理解,我不反对,但是想要真正解决问题,一定得从底下开始弄,但是风气就是想快见成果。当然我也是有幸,因为你没这个(成功经验)人家根本也不带你玩儿,人家听说你的案例才来邀请,所以你说怎么弄,他用这个(逻辑)来思考问题。
所以当我们不能把心放在当下的时候,你马上要有一个自我的觉知就是你的安全感低下了,不敢面对现实的生活,你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包括宗教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信,宗教就是不能讲当下,因为当下就戳穿了,我拜佛了怎么股市又赔了?这个佛不灵,所以必须得支一个招,这个拜的不诚,得多少拜,得多少年以后才见效,得先一竿子给支出去,它不能马上兑现,否则这个宗教立刻就穿帮,所以这个时候它只能讲过去和未来。
愿意讲当下的人,一定是安全感满满的,敢于生活,敢于做事情,敢于去找自己的乐趣。因为人只能活在当下,不能活在别的地方。这个是深层次的问题,而且给弄成集体无意识的恐惧,互相的感染,没法面对当下,就是忍着吧,先当房奴吧,怎么弄吧,都是这样,我们没有当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要算计,这样的付出,将来能不能有回报?如果没有回报那就有崩溃的危险。所以这些跟着导航仪走的孩子一旦没了导航,就没辙了,到不了地方了。原来我跟着你走非常苦逼,但我能到地方,现在不行了,结果就崩溃了。然后一测那个心理量表,结果特别滑稽,他说我很焦虑,但是一看量表结果,强迫很高,为什么,他要强迫自己跟着老师走,他不愿意,但是要强迫,现在(上大学后)没人强迫了,然后就焦虑了。没有一个可以扶的拐棍或者能坐的轮椅了,突然焦虑了。他还是强迫没解决,所以强迫引发的焦虑,如果这时候你去做焦虑治疗,就死了。
这个我认为和自学是一样的,你要先搞清楚,醋打哪酸,盐打哪咸你得弄明白了。我们却不,我们就说不要焦虑,我们有24个价值观……这些不解决当下,那这个事就是无解,只能让你忍。离高考倒计时,咬咬牙就过去了,大家都玩这个。我们自己过日子也可以看出,如果你老想过去,或者老想未来,那一定是现在有问题了,这是一个自我觉知的方法,对自己的洞察力就在这里。你没法活在当下,现在吃的也不多,反正喂饱了就行,卡路里、维生素够了就吃,你自己想想这样的日子怎么过?
这个是深层次的问题,五四以来弄的都是科学概念,都觉得,他们有炮,我们也有炮,他们有枪,我们也有枪,就完了,科学的思想没有。你自己去看,其实清朝的热兵器的配备并不比八国联军差,但大家都是胡来,没有那种训练,没有工业化的训练。你看德国工人上街游行,他们没有军训,但是在大工业生产的熏陶下,生活当中,他也必须强调协调一致,互相的关照。我们现在没有,所以一打仗的时候就散伙,通常场景就是:我们俩是老乡,我们往一块儿跑,他们俩是老乡,他们往一块儿跑,就这么玩儿。他又没有社团,但总得有一个归类吧,有一个分类方法吧,不管是按岁数,按性别还是按什么,总得有个方法吧。然后实际就是按地域分。
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这个自学不是自己去把理论搞明白,自己啃课本,不是;是你自己要通过这种学习,把自己准备过什么样的人生给搞明白。这里面(书中)说我们搞的是科学本位思想,而没有对科学的精神的阐扬。一个动作,灯就亮了,哦,电点亮的,完了,到此为止。它都是碎片化的科学的认知,然后用这些东西去弄中国的社会,结果就是社会哪儿都不像,学西方也不像西方,自己也不像自己,七林八怪。他们认为可以用科学态度去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可以通过算度来解决,甚至(马克思)用科学规律来推导,你们将来过什么样的日子,然后说这是科学的,所以他是对的。
但是现在诺贝尔奖经常有心理学家获奖,特别有意思,大部分奖是在经济上的,人的非理性行为。就是你所谓的科学,遇到人,不好使。如果人都是理性的,那价格规律的调整应该非常有效,那么为什么现在追涨杀跌?他有恐慌,要是再涨咋办?他这么想的,而不会按你以为的一看市场信号亮红灯,马上就停车,绿灯亮了马上就上,他不会,他马上其他的思想就出来了。然后整个的市场就弄的不像样,一团混乱。
另外我们自己在搞学西方的一套政治的时候,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也是乱的。美国讲政治家三大要素:热情、责任感、判断。我们现在只有热情,没有其他,先把大家忽悠起来再说,然后弄的这个工程也好,那个工程也好,完了之后谁也不提了;鸟巢,弄成这德行了,完后没人吭声了,得了。
全:
责任感都是对上级的责任感
梁:
责任感的问题在于你的是虚假的,那种责任感是什么,还是功利,因为你能提拔我,所以我要让你高兴,否则连这个都没有,一切还是功利的。
这样一个情况下看出我们原来的那个东西(传统政治抱负)可能缥缈一点,但是它是深远的。要做圣贤,要怎么怎么样,要修治齐平等。现在不管,就是算账,精致利己主义,就这么玩儿。现在就是包装了科学外衣的功利主义思想在中国大行其道。我非常科学,这样弄就能怎样,那样弄又可以怎样,但是所有的公式都是得失,趋利避害的。
佛教在乎的是非判断,超弊害的,没有罪福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在思想脉络上如果整不明白,你在底下鼓捣,没戏。一弄就是得失,以后没意思,所有东西都没意思的,就都觉得不值。人生的乐趣完全没了,所有的人生都完全用指标来算的,多少钱,多大的房子,然后完了。在他(梁老)那个里面最起码有一个高兴,他有一乐。
(我接诊的)有一个焦虑的学生就是得拼命刷题,不刷题就死定了,所以我在许多群里,把我拉进去一看,就是焦虑都满满的,就是英语老师怎么怎么样,什么教学的技术,整天的在高度的紧张和焦虑,你和他交流不进去,你不能说他不自觉,他拼了命在学,但你发现,越学越恐慌,因为他在人生的乐趣和取向上是乱的,他自己找不着北,他真的坚持不住的。这里不是说我要超然物外,而是比如说今天这顿饭我好好吃,大家见面呢很高兴,这个是能谈的。那个孩子焦虑到什么程度,就是我问你跑步能不能放松,他说也不能放松,怎么呢,他边听英语边跑的。我说你是把自己当成移动硬盘了吧,完全没有感觉,都是概念。你不能说他没在自学,但你看看他把自己给学成什么德行了。所以你在这样一个不断去弄阅兵式的环境下能不能HOLD得住,这是个关键。
耿:
那种在高压强度下仍然HOLD得住的人,算不算毅力很强呢?
梁:
不是,他还得通透,还得有洞见,他得能看穿这里面的东西。他不是硬去坚持,我一直以来的坚持不是靠硬,而是看明白了,这没用,对你的人生品质没有用。对于你达到目标可能有用,但是对提高生活品质是没有意义的。你非常苦逼的在刷题,你根本不喜欢,但是你要刷;你根本不喜欢这个专业,但是据说收入高,所以你选择它,是这么个情况。
程:
那么要是有人可以意识到这个对于我达到目标是有用的,让我更愉快是没用的,怎么做?
梁:
这里你要先明白自己是把它当战术还是战略,比如韩信受胯下之辱他是战术,他不能整天在那儿钻啊,它不能把这个当战略啊,那就没有未来了,你不能这辈子就这么干,那就死了。
程:
我自己感觉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是分几段的。我自己在公司里会有很集权的现象,你若顺着他的意思去做会很容易完成,之所以我坐在现在这个位置是因为去年负责一个非常贵的产品,而这个产品我自己其实知道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但是我知道只要完成它我会很快得到自由,我可以快点离开它。但是中间有时就会有这种感觉,你是为了继续过这样的日子,还是要快点从这个地方离去?每次把我逼到需要做选择时候,我就意识到我需要新的能力,摆脱这一切,这可能是我自觉的一个动力。这类事情可能经常会在生活里发生,无法做到不去功利,因为有时候不功利也会影响你的快乐值。
梁:
问题的关键是你得明白你得有,你不能自己把这个东西从选项里排除,我们在就有很多直接就赤裸裸的把选项排除的事情,现在社会上有倡导,去被主流的倡导,而且有时候弄着弄着就会不自洽,比如说这回好像还算仁义,说不像工作猝死者学习,但又让大家整天这么焦灼,那怎么办?问题还是没解决,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它只能进行号召。那你说能不能先从法律角度讲,保证双休,然后各负其责。再有你必须得承认,人就是会犯错误的。(若是要求)就是不许出事,这个做不到。他只能让人更焦虑,就像之前讲过(鸦片战争前期)清朝两广总督,(开口岸)皇上不同意,我只能先拖着,等到我卸任,他只能这么玩,大家伙玩击鼓传花,完全不去处理问题了,但是最后那个雷响的时候结果一定是天塌地陷的,因为所有问题都累积了。
这实际上是一个有没有勇气的问题,其实最大的勇气,就包括之前讲到的西方的科学是为科学而科学,我们不是,我们总想着科学能不能赚点什么,学一个什么炒股的技术,学个什么软件,我就能赢,他都这么玩的。他对于那种超越利害的那种乐趣的追求完全放弃掉了。西方有很多人是认可科学本身就是乐趣,包括爱因斯坦到美国去,给他那么高的薪水,他说给我3000美元就够了,当数学家不用花很多钱,他是这么想的。不是说他放弃对物质的追求,但是不能只追求这个。我们现在就弄成了两个极端,从精神分析上讲其实特别好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贪官好色好财,就是由于他极度的压抑,就是他的超我太假了,所以他的本我就极度的失控,自我就很脆弱,然后就这样,他一定要贪财,一定要有情妇,为什么,因为他扭曲,他自己和自己不能融洽。就是那个东西被挂在墙上,底下是另外一套,他的人格是分裂的。我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这么抓贪官一定抓不完,因为他解决不了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平衡,你非要让他弄成这个德行他就必然分裂,分裂以后他一定就得出这个问题。那个超我太高,本我的力量就变得非常大了。
我们都是把科学当做知识来用,当成一个螺丝刀来用,而没有对科学本身的那种谦恭和尊重。“因真理而自由”他不管真理有什么用,但是要有对真理的一种渴望和追求,而我们不是,我们就要好使,那这个精神没了以后就会变成一种极度的功利主义,这就是五四的结果,它非但没有真正把德先生、赛先生弄进来,反而把这两个搞的浅薄化了。因为大家太着急了,囫囵吞枣,根本来不及(消化)。
我最近也上了一当,买了本《科学与宗教》,结果差点没读吐了,(书里)一大堆数学公式,反复想证明上帝是否是存在的,什么天体运行的规律一定是这样,日心说……我本来想看从这个角度到底有没有可能学清楚科学与宗教怎么能相辅相成,因为宗教其实是科学的母体,他想用科学证明上帝的化身就是数学,他可以无所不在,可以非常完美的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要命的就是达尔文,他杀死了上帝,因为演化是无方向的,要是(进化)不断是向好的方向那么帽子就可以交给上帝,但是现实是有很多奇葩的东西解释不来,明明不利于个体生存的东西不断的出现,那上帝怎么回事?上帝想让我们受苦,这种解释说的自己底气都不足,作者特别想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解释,看得我想吐,但是硬着头皮把这本书啃下来了,但是我后来也明白,他为真理而真理,他不管别的。他从哲理,逻辑上来推断上帝(存在)是可能或者不可能。这里面肯定没人赚钱,或者从而晋升,发SCI什么的,但是就是有乐趣。
程: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我昨晚和一个客户聊天时,我在试图从逻辑和道理的层面论证这个事情不管是不是和我合作还是其他人都应该这么做,但是我发现当你这样说时他压根不相信你,我捉到了他不信任的眼神,然后接下来的对话里我把我的利益关系放了进去,我说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以内我有其他什么事情,然后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对我也是有利的,结果他反而接受这件事了,就是说他思考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超利害,反而会认为你在骗他,反而我加点私利在里面能让他相信。
梁:
你记得我曾经讲过:两点之间,曲线最近;你又想走直线。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6月底要在山东大学开一个会,研究我祖父搞乡村建设的问题,这个乡建为什么搞得慢,我和我父亲探讨了半天,他说通过让农民种棉花,提高富裕程度等。我问那商业有变化吗?父亲说没有,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人一直鄙视商业,包括蒋介石(统治)时候就不太在乎商业,党就更不在意商业了,但是唯有商业才能使得生产发展,这就是阴向阳中求。他老认为那个东西(商业)不生产,他特别具象的看,就是你不创造财富,你(商人)只是把货物搬来搬去,然后你占大便宜了,他老这么想。特别狭隘的看,这边种出来两吨玉米,这个好;那边生产一匹布,这个也好。他是这么看的,而不是从一个系统的角度来看。所以如果你从资本论的角度来看,那商人都该杀死,这都是什么价值观?所以说如果在思想的深度上看不透,这不是盲区,而是“盲维”,少了一个维度的认知,那就死定了。
我们就是看问题缺个维度,我们以为想的非常好。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所说的在规律面前我们还没有做到保持谦恭,保持谨慎的态度,这样下去不出事其实是奇怪的。很多东西的发展一定是超越你自己的想象的。比如发展共享单车时你哪里知道会把偷车的给干掉了?所有的发展一定不会是设想出来的,而一定是走到那才会发生。当然我们要去创造,那是另一个概念。但是你所有东西都是齐步走,都是正步,你自己觉得他怎么去创新?这个本身就是矛盾的。一边要告诉你:懂规矩,守纪律;然后要求创新。这不是很变态么?非得打架不可。中国企业也是,规模可以做得很大,但是一到国际市场,发现自己玩不转了。他最后一定是一个层级的差别,不是说我努努力就搞得定的,层级的差别是没法弄的。而你老还不甘心,老还“厉害了我的国”,非出洋相不可。不在一个层级上玩,自己自嗨,没有用。
我们想说我们自己,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沉住气,这是问题的关键。
梁:
这里有一个根本问题在于你面对的是人,人性的那部分你如果不尊重,那一定要出事。
冯:
现在有机关调成,有些单位不知道应该怎样调整,十几个中心的那种大型官僚机构要变成四个中心,然后大家都在天天焦虑的学文件,一天打三次卡,我觉得简直是非人的生活。
李:现在各种玄学大兴,是不是就是个(混乱的)苗头呢?
梁:
他就是因为安全感底,包括一些外来宗教的兴盛,因为就只能往未来找,因为顾不了当下,这是最大的市场,一点办法也没有。
冯:但是国外也普遍信宗教,他们不是因为安全感的问题吧?
梁:
他的那个情况是自由度太大以后的没有皈依感,我的一个亲戚曾跟我说,出国后就特别向往社会主义,国内所有银行都一个利率,所以你省心了,国外一会儿说这么贷款可以便宜多少,那个银行又能优惠……自己算得头都大了。社会主义就这一个(利率),国家规定的。你看有很多东西在别人眼里看是另外一个概念,比如农民他种地盼着下雨,旅游的游客希望是晴天,这里没有好坏的问题,只在立场不同。
这里的问题是他的管控不断的深入到你的生活,甚至头脑里,他对你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你自己如果心里不清楚,自己不去捍卫你的心灵边界的话,你自己就要出问题了。你若不捍卫,它就蔓延过来了,就把你不知不觉中俘获了。
程:
我这次从上海回来后有些失落感,当时我从体制里出来了,我觉得不论外企还是民企,我自己有能力,我一定会比在体制里过得好,基于这种想法。我在外面成长也挺大的,但这次我回来发现大家在体制内可能受着各种各样管制,加班啊,党建啊,我当时看着很烦恼的那些东西,但是他们到了这个时候就知道自己该考试了,过一阵就知道要升职称了,然后他其实只需要跟着大家这么走着,自己也不用操心,平时回家也没什么压力了,可能就做做饭什么的,可是我的压力在于不确定性,我去年焦虑到最严重的时候连早晨起来完成刷牙的动作都不成,而且当我向老板倾诉的时候,老板还在给我施加压力,她说: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去解决。结果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我办好了一个20万的单子,一下子就好起来了。我当时选了一个感觉比较顺从自己内心,又活得不累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后来发现怎么活都会很累。他们要去应付那个东西,我在这边要应付我的。
梁:
这里你要先明白自己想要哪种后悔?是没尝试过的那种后悔,还是试过以后这个不适合我的那种后悔,你得选一个,不可能什么都有。你这么想,你去冲浪,你就享受冲浪,冲浪没有规定动作,你没法保证掉不下来。
冯:
我有些想分享,因为我也是从你(程)那个时候过来的,我是师范毕业,我们所有同学都是去当老师,当时想离开教育口是很难的。我的同学有的得干满五年,然后给学校交一大笔钱后才能出来;我去实习的时候,带我的是年级组长,非常资深的老师,她的家就在学校后边的一个小平房里,我那天去给他送钥匙,就感觉那个小平房又黑又暗又小,我当时就觉得都年级组长了,资深教师,怎么就住在这样水准的平房?我当时的感觉好像自己一辈子就看到头了,所以我就毅然决然跳出了教育口,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自己一直是顺从着自己的内心,后来发现自己还是想去做文字(相关工作),所有又去报社,一直在做自己所喜欢和擅长的事情。但是这个过程也有很多问题,不在此细述,直到前几年我们大学同学建了群,看到那帮(同学)都已经很超脱了,有追求的都做到年级组长,我们毕业那年有师源断层,毕业的同学基本上都可以在单位挑大梁了;那有些不愿意追求职称的就特别闲散,一周上四堂课,天天晒自己吃的美食,旅游照片。人家按部就班的走下来,现在享受成果,生活也很好;我现在在当记者,现在记者的职业门槛是一路在跌,随便谁都能当个主编,但是当老师的门槛是一路上升,西城区一个排名倒数的学校招聘都恨不得硕士、博士,而且还很难进,这些年职业情况的变化是很大的,我当年不珍惜的教师岗位位置,现在变得非常金贵。那回头想,我是不是后悔呢?当年自己这么折腾,又跳槽,又创业,有没有价值?我觉得人不能走回头路,那个时间顺从自己的选择,就不要后悔。如果真的把你放回那一刻,你可能还是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梁:
这里面看出,你的潜意识就是你的命运,你自己在这个时候判断选择的权重是怎样的。他没有那么多的判定依据,比如说我从45岁改行搞心理,谁能给我保障?没有,但这个弯就这么拐过来了,别人听着都觉得震撼,我当时没想这个,就是觉得(前工作单位)太无聊了,关键是你对无聊的忍耐力是怎样的?再有就是你能否和现在的职业自洽。
我自己的优点就是好奇心强,啥都愿意去琢磨,但是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一定不会去培养好奇心,都要规范化,格式化,这其实是很要命的,而且把学生所有的时间都占据了,他没有自由时间,没法让学生自觉自主的去探索。崔健讲过为什么他们部队里的人都比较牛X,比如王朔、姜文,他说文革的时候,部队家庭里父亲一般都被派出去支左了,家里就剩妈了,孩子又多,管不了,我们野蛮生长,所以我们那个自我的个儿大,所以磨掉了一部分,还剩下一部分,你们的自我磨没了。没有自我就一定没有创新能力,因为所有的创新不是由你发生,而是经由你发生,你把很多信息汇聚,加工,按你的想法重新组合,然后出来一个新东西,才是创新的途径。比如说我当年去搞充气脸盆的设计,我即没弄过脸盆也没弄过充气玩具,就是各种好奇心获得的信息,在70年代时国外开始搞充气建筑,我就非常感兴趣,纯粹出于好奇,曾认真看过他们充气结构的设计原理,等做充气脸盆时的技术难点是脸盆的帮怎么设计让它能站起来,把我难了一个月,有一天坐公交车上班,那天特别挤,有一个女同志的羽绒服贴到我脸上了,那一瞬间,我看见羽绒服的行线提醒了我,后来做充气脸盆时也加入行线,但是上面一圈是通的,中间是焊死的,就形成一个个的小气柱,然后脸盆就站起来了,问题解决了。这不是由我,而是经由我而发生。你的思想足够开放,涉猎面又广,你不断的搅和,就出来了。包括后来搞科研,从工艺上、工装上、测试装备上的创新都是自己弄。那时我和王仪应该说是天作之合,他动手能力特别强,基本上我只要有构想他就能做出来,车钳铣铆焊他都可以,当时我们合作很爽,能够快速的做出来很多东西。
- 回想自身中学时期和工作后的生活经历,请给你所接收到的学校教育各学科从最务实到最务虚做一下排序,并说明理由(你眼中能代表当代的务实需要拥有什么属性?)
- 设想若有以专讲务实为目标的教学体系,是否可能在当代培养出具竞争力的人才?
冯:
我看过吴军的《大学之路》,书里分析了国外的教育,以北美为主要应用的教育体系为博雅教育,以德国为标志的为洪堡教育,后者比较偏向于专科分类的,很实用的技能培养,这种理念后来传到苏联,进而传到中国,所以中国在建国初期的教育体系都是洪堡教育制度下的分类,各种工业大学等等非常专科化的人才培养。这种体系下可以快速塑造培养人到一个专业领域里,然后越走越深;美国为首的博雅教育体系,大学的头两年根本不选专业,学生什么都要学,尤其是人文,历史,等你有各种知识涉猎后再思考自己人生的方向,然后在大三大四甚至法学院和医学院要求大学毕业以后再进入到以职业为方向的学院去。这种教育培养的就是综合能力,然后在自己很清楚自己擅长的领域后再选择深入去发展的方向。比较夸张的像耶鲁、哈弗的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经常会说:如果我大学的学生只为了毕业后寻觅到好的工作的话,那简直是我们大学的耻辱和失败。他立志于培养社会精英,当然这里也说不出好坏,毕竟哈弗、耶鲁出来的已经是精英了,我今天看到一个文章,说哈弗出来的学生至少1/3是在金融咨询领域当金领,或者出来创业等等,我想说从虚实来看可能洪堡体系更容易培养出人才,但是说不好哪个更好。
梁:
我认为这里要分阶段,第一必须得有实,包括如果不去炒菜,做家务,其实对人是一种伤害,我多次强调,孩子做家务是他成长的需要,而不是你们家没小时工了。我们从概念上老是从具体的功能上看,这里你的格局的大小,在于你尺度的大小,你想在多长的时间尺度内看到结果,穷人总想立竿见影。有一次电视台采访加拿大来中国说相声的大山,问他做生意赚了赔了,大山非常滑头,说:有赔有赚的才是大买卖。这确实是大实话,你比如开个煎饼摊,卖不完可以回家吃了,可以降低风险。关键是你在一个什么时间尺度内评估教育的结果,我们现在都想越来越快的解决问题,只有科学的思路,没有科学的理念和精神,老想着在瞬间内解决问题,那所有能瞬间解决的问题一定是浅表的。深层的问题一定不会在几秒钟内解决,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格局,或者说心胸的大小,和你的时间尺度一定相关的,看你在一个什么时间尺度上去要求结果。
有评论麦当劳化的出现造成了医闹的增加,在麦当劳所有东西都可以是标准的,只要你去吃巨无霸,到全国各地都是一个口味,那他(百姓)就认为这个事情是绝对可控的,我给你钱,你就得做好,不可以出问题。这和我们现在的领导的思路是一样的。管不好提头来见,都是打仗的节奏。有一个搞精神分析的人直接说:这透着匪气。这样一个总体的思路以后,大家都是短视的。都是迅速,都要快,所有都不能容忍一个过程,而且不愿意有过程。这样中国人整个对问题的思考就深入不下去。比如中国搞的飞机的问题,因为我是搞材料的,对这个很清楚,我们整个的奖励制度是有问题的。中国的材料问题是要了亲命的,材料根本没法仿,我们老以为弄个配方就行了,其实是大错,材料的东西特别复杂微妙,根本不是能从配方上分析出来的,何况工艺还有差别,比如我告诉你西红柿炒鸡蛋的材料,你拿去炒,做出来肯定不一样,火候,出锅的时间,葱什么时候放等等,这些都是工艺,那个东西是化验不出来的。我们都是首长的意志来决定,比如说我们需要战斗机,然后就去搞,没有规律;国外是先搞发动机,再搞飞机,我们倒过来干,结果就是干不动,效率低,损失大。先穿鞋再穿袜子,看不行再退下来重新弄,都是成本。还有就是你面对的一切因素都是不确定的,但是又由一个中心发布指令,你觉得那个棋子能思考么?他能做出自主反应么?那每一个棋子面临情况该怎么办?找党中央,必然如此。
我们之所以强调要对个体培养,对个体尊重,就是因为在那一瞬间,个体要思考如何去解决问题,我们解决问题就是拿钱砸,为了献礼,为了争口气,就拿钱砸,这个也让特朗普害怕,他发现你不是社会主义,你是国家资本主义。你可以拿举国的资源和他对赌,这个没法玩。
关键是在细节,虚和实,得在一个大的时间尺度上去看,否则就看不远;但是不深入细节,就没有感受。